东北那旮旯原来没多少人,一望无际的大森林、大湿地、大草原。从清朝末年开始,关内闹饥荒,一个个便拖家带口跑东北寻吃的来了。这些人中,山东人居多,起初一个个黄皮拉瘦的,但毕竟都是大坯子,见野花野草野兽遍地,顿时来了精神,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没几个年头,便都缓了秧,男的粗犷彪悍,女的如花似玉,把整个东北弄得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百十来年过去了,人丁跟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那叫一个茂盛。有时大家栖在一起拉起呱来,唠不上三句,便会有人“哎呀哎呀”牙疼似的用力拍着对方的肩膀说自己是山东人,什么济南府了,曹州府了,登州府了,都是山东老乡。
山东人倔强。小时候,经常听别人说山东人比较奘性,打定的主意,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所以人称“山东棒子”。尽管有些贬义,但从中也看出了山东人的直率,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也没那么多花花肠子,性情刚烈,宁折不弯,要不历史上怎么会涌现出那么多英雄呢。孔子扁鹊鲁班这些名家名医名匠自不用说,就连王羲之李清照蒲松龄这些咿咿呀呀的文弱之人,也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更别提什么呼风唤雨的姜子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孙武、三气周瑜的诸葛亮、闹得大宋江山鸡犬不宁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了。硝烟散尽,山东人铸剑为犁,到处都是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和平景象,骨头的硬度却丝毫不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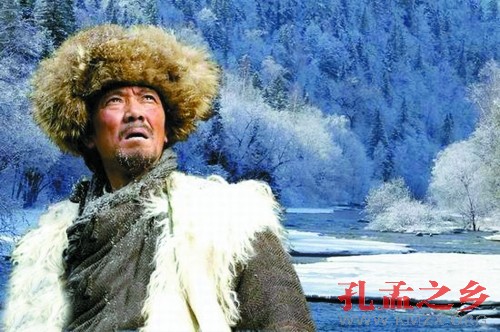
山东人热心肠、豁达、豪爽,侠肝义胆。一干人马出行,当中如有山东人,尤其是山东大汉,心里便托了底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些年来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山东人老鼻子了。去年我在北京培训,班里组织活动,去鸟巢和水立方参观。那天天公不作美,刚走下车便大雨如注。此时山东籍的赵大哥早已撒开丫子没了踪影,可转眼之间又湿漉漉地跑了回来,怀里多了一抱伞,大家心里顿时晴了天。还有一次,班里的几个人闲来无事,逛到朝阳区双桥中路的一家路边摊儿,要了一箱啤酒,正喝得起兴,突然身后的几个人吵嚷起来,甚至还有人抄起了啤酒瓶子,吓得邻桌的人四散而逃。当时我也两股战战,几欲先走,而赵大哥却纹丝不动。这时候,有个家伙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摇摇晃晃地直奔我们而来,一边比比划划地向我们示威,一边大舌郎几地骂着什么。等那个家伙凑近了,一直埋头喝酒的赵大哥突然吼了一句,纵身跃起,一把扯住那个家伙的衣领子,扬起的拳头攥得咯嘣咯嘣直响,不但吓得那个挑衅的家伙面如菜色,也把余下的几个小子震住了,最后一个个灰溜溜夹着尾巴逃走了。
山东人认亲,家族观念比较强。这从一些地名上便能看出一二来,什么荣家庄、姜家庙、宋家堂,本乡本土一堆一撮儿的,大家小户非常集中,乡音浓郁,亲情浩荡。今年春节一个朋友回了一趟山东老家,临沂。朋友在家是老小,因此在辈分上比较靠上,即人小辈大。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今天东家扯,明天西家拽,结果男男女女百十来口,记了这个忘了那个,最后也没几个能叫上名字的。而大家倒不在意,这个叫叔,那个叫伯,一个头发花白的还叫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响头。山东人讲究,只要是辈分高的,不论男女,不管年龄,不分身份,打心眼里高看一眼,这种从骨子里透出的对长辈的尊敬,被山东人一代代延续着,传承着。
东北养活了山东人,山东人也对东北的文化的兴起勃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地处北疆的黑龙江,主体文化本身就根植于山东,一些习俗也来自于山东,许多方言仍留有山东人的痕迹,如“日头”“硌应”“差不离”“不济”“出溜”“刺挠”“楔你一顿”“瓷实”等等。有时,山东人和黑龙江人聊起天来,如果山东人不带浓重的口音,真的很难分清谁是山东人,谁是黑龙江人。
至于我的老家是不是山东的,我曾问过一些长辈,他们都说是河北保定的,这使我很失望。我曾设想过,五百年前我的祖先就应该在山东的一个什么县,当过一段时间手下有衙役的七品芝麻官。后因痛恨当朝昏庸无道,退隐山林,花前月下,儿孙满堂,百岁那年无疾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