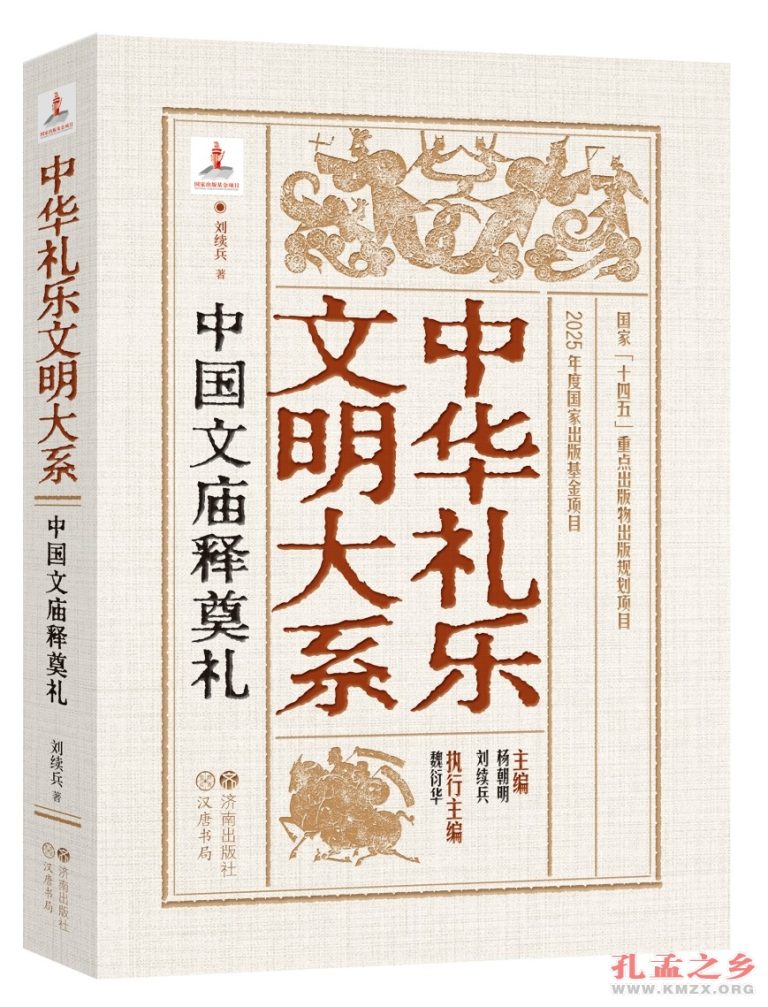薛仁明大约是近几年来华人文化圈新蹿起的,最为闪亮的熠熠明星之一 。说“蹿”,似乎市侩而鄙陋,但这字眼的动态感的确颇能说明他的出现所引起的注目之广及传布之快。外表的原因,是在于他写作论述的对象是抗战以来千夫所指的“汉奸”胡兰成,以及近三千年来形象不坠的至圣先师孔子。而此二人,在他眼中笔下,皆充满“反骨”,又同样有着天地之始的鲜活生气。“孔子与汉奸”,在这个凡事讲究莫名其妙“创意”的社会,这样的创作思维,套个周杰伦爱说的字眼,够“屌”(这实在是个极粗俗却又极具生命力的词汇)吧!
然而,薛氏才高学博,文章清朗挥洒,满是风情:明明说的是深沉哲思,却又显得云淡风轻;写的是生命学问,反似船过无痕。他不想教训谁。也许正如其师林谷芳教授所言,以气象之笔谈史论事,“就有一番自家风光”,而这正是薛仁明一出手就掀起江湖风波,令人目不转眼的实情所在吧。
要认识薛仁明不难,目前为止,他著作不多;但是,真要彻底了解,却也不易,因为他的学问很大,文史哲禅道艺,多元博杂。但无论如何,读《孔子随喜》一书,观热闹也罢,看门道亦可,精彩趣味,不在话下。
在《孔子随喜》一书中,薛仁明贯穿古今、出入经史,同时又谈禅批道(宋明理学之道);他以风姿绰约的文字,企图重塑一张可敬可亲、人性又诗情的孔颜。字里行间流泄作者对一部《论语》熟极,通极,透极,又款款深情极。说他是孔子的超级粉丝,绝不为过,但他丰实多样的学养才情,一望即知不是盲目崇拜,人云亦云而已。
《孔子随喜》笔法特别的是,作者总由平常的生活经验出发,譬如《风乎舞雩》一文,他就从看似不相干的西湖之游入手(注意,不是曲阜),从依然料峭的仲春联想到春服既成惠风和畅的暮春,带出《论语》中最美的一幅风景──“风乎舞雩”。借孔子对听似无心、却若有意的曾点之志喟然而叹的举动,进一步探索:我们对孔子“真的那么熟识”吗?再辅以一桩桩一件件孔子在栖遑奔走、又困厄交逼的难堪狼狈中,仍保有乐以忘忧的豁然大器,提醒读者:经过程朱道学诠释的孔子,那真的是孔子吗?
作者以为:因为孔子“感而遂通”的诗人特质,使他得“通达于人,通透于己”,使他可以高于时代;尤其孔门诗教的关键:那一个“兴”字,更使孔子可以大于所有苦难。因为“兴”,所以他虽然仆仆风尘十数年,虽然他“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但也仍能逐渐迈向生命之境的孤峰顶上。他不似道学家那般一丝不苟,他总是“无可无不可”,但世事了然于胸,红尘万象于他,历历分明啊!
孔门课室中,虽说总诗礼并举,但永远诗先于礼,而后通于乐。这即是“感”、即是“兴”,也使孔子的诗意世界与世人无隔,如此礼教,何能杀人?五四要打倒的,是借孔家开店的道学诸君吧!
《孔子随喜》里头某些观点,我相信,必定不为某些迂腐的儒者所喜。但正因这种不喜,是不是才更证明了这的确是一本斐然成章的大气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