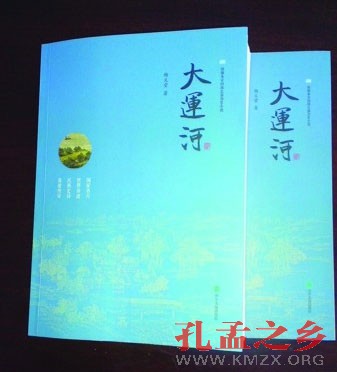二十年前,笔者写过一首关于大运河的歌———《运河从俺门前过》:“天上有一条银河,那是人间美丽的传说;地上有一条运河,那是中华儿女亲手开凿。这条河北去长城送温馨,这条河南下天堂添锦绣,这条河风雨沧桑八百年,这条河号子声声写春秋。啊,古老秀美的大运河啊,人间奇迹,天地传奏,你是勤劳智慧的颂歌。东西有长江黄河,那是华夏秀丽的理由;南北有一条运河,她把中华文明传播。这条河天天从俺门前过,这条河南来北往荡飞舟,这条河浪花推着富裕走,这条河两岸金窝连银窝。啊,古老传奇的大运河,丰功伟绩,任人评说,你是世代传唱的风流歌”。
此后,一直盼望着有一部传颂大运河的文学或影视巨作问世。今天,当翻阅着杨义堂3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大运河》时,心中感到一丝欣慰。
作品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篡位登基拉开序幕,又以济宁分管治水的同知潘叔正通过实地勘察,以大运河济宁段有二百余里不通航阻碍南北运输为由,屡屡上呈状子治水遭拒,终借永乐皇帝不适应金陵的环境,意欲重开运河迁都北京,揭开了贯穿全书的主题:即继吴王夫差开通邗沟、隋炀帝开通以洛阳为中心运河、元朝又将大运河裁弯取直之后,第四次对大运河施以大手术———修通山东会通河一段。
翻开《大运河》这部作品,作者没有简复历史,乱写趣事,而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扣紧主题,巧构故事,写活人物,打动读者。
滔滔运河水,北起燕山,南入苏杭,南北几千里,走过上千年,历经沧桑风雨,饱尝喜怒哀乐。要写好大运河,可谓斗大的狮子,无处下口。可作者独具匠心,乍看,作者没有编出扣人心弦的曲折故事勾住读者,没有用露骨的情爱描述去俘获读者,更没有以“挖土、运土、筑坝、打桩、吃饭,睡觉”等简单的文字堆叠填章充数,而是以淳朴的白描手法,一笔笔勾勒出当年华夏文明史的重要篇章,也是大运河成败之笔———南旺分水工程。让读者又一次重温了那段感人的故事:汶上农民出身的治水能人白英,在工部尚书宋礼三次登门求贤无望愿与其结义时,欣然跪拜,同意任治水总师。并戒酒谢客,全心治水。为确保大运河济宁段有充足水源通航,精心设计出精妙绝伦的南旺分水工程:首先,截大汶河水补充运河,在汶河建戴村坝堵截汶河水;其次,开挖小汶河,引入大汶河水至南旺;其三,挖泉河把汶上东北以及兖州所有泉水引到南旺;其四,在南旺建分水枢纽工程,使小汶河水流经过竖槽直接补充大运河。并在小汶河口建成“鱼嘴”,让其自行调节水量,三分向北,七分向南。其治水工程的科学含量被毛泽东主席总结为“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自明代工程建成以后,大运河四百余年畅通无阻。主题故事的成功是整体作品成功的基础,这部《大运河》,再现了明朝初年修复运河的历史,让人们认识了华夏儿女治理运河的勤劳、坚贞和智慧。《大运河》的另一个可读之处,是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编织了一个个曲折蜿蜒、环环相扣的故事,使你融身于当年的其情其境,推不掉,抹不去,惦念着一个个人物的命运:小工头颜开不让河工李老大回家拜堂娶妻时,白英老人送女上河与李老大成婚。白英三拒宋礼请贤后,与其结拜兄弟出山治水。江南才子潘叔正中举济宁为官,妻子巧云贪财出轨。陈喧痴情多次险境寻救茅毛,宋小蛮追情郎不成下嫁给潘叔正。杜知州为升官献祥瑞臭白鲤鱼,宋礼受杜晓言陷害含冤下大牢。以及白秀兰历经磨难终与宋大牛成正果……尤其是重笔描绘的溃坝、断粮、瘟疫、白英率河工赴京都解救宋礼等章节,将故事一次次推向高潮,并由此走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执拗认真、不求名利、爱喝几口小酒的治水首要功臣白英;清廉耿直、铁面无私、又极具人情味的工部尚书宋礼;敢于进言、一身书生气的济宁同知潘叔正;佛面兽心、阴险歹毒的和尚谋士姚广孝;见风使舵、吃喝嫖赌,坏事做绝的济宁胥吏颜开;活泼可爱、敢作敢为、情窦初开的宋小蛮,美丽善良、忠贞守孝的朴实村姑白秀兰;还有陈喧、灵芝、朱高煦、杜晓言、李老大、张巧云等二十几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到你眼前。特别是人物形象的描写,把其独特的个性和棱角充分展现给读者,这里不妨摘录几句:肥胖的鲁王像皮球一样,一下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大叫一声:“好”;姚广孝一双三角眼满是凶光;李大娘有气无力地说:“没啥,咱就是一个草民,死了,就埋了,修河的事,比天大啊!”张巧云早已心花怒放,盘算着五两银子就要到手,斜眼看着颜升,越看越顺眼,心猿意马地说:“穿一条裤子怎么了,愿意和大官人穿一条裤子的人有的是,一般人还不一定能穿的上”。宋小蛮与陈喧目光相对,她一下子抓住陈喧的胳膊,惊喜地问:“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谢平江伯救命之恩,我这条命是你给的,啥时要,拿去”“不,我就要嫁给你”这些鲜活的描写,推动了情节,写活了人物。文学是人学,写活了人物,就使作品成功了一半。《大运河》这部小说,让大家又一次分享了这段历史传奇,相信她也会成为世代传颂的运河风流歌。
当然,综观《大运河》全书,在故事布局设计上,语言的时代性与进一步简炼上,特别是以南旺分水工程为中心的故事与这本书的主体关系处理上,仍有一些可商榷的地方。尽管如此,笔者仍以为这是一部可以一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