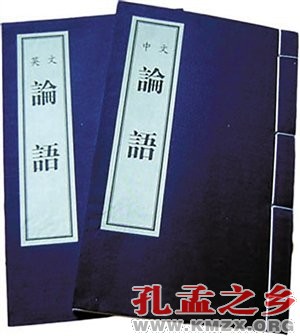
1 仁与爱是自尊心态的情感基础
《论语》论“仁”凡一百余次,“仁”是孔子学说的本源和精髓,其本义为相亲相爱,起情感之功用,孔子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范畴,要求人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给予我们一种心态启示: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要把所想之事推己及人,放到对方的立场考虑。孔子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表现的是一种人格独立与尊严的强毅。人的价值不仅在于自己应当受到尊重的独立意志,更在于其是一个自我主宰的主体,有着自觉的道德追求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每一个人都可以阐发内在道德资源,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其独立人格,同时人一定要有情感。情感一方面表现为对他人的竭诚友爱,即“君子学道则爱人”;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不道德行为的憎恶,即爱憎分明的情感。“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爱憎分明的情感只有仁者具备。因而构成自尊心态的另一情感基础即“爱”,是孔子的核心精神。“爱”作为自尊心态的情感基础,在人们行为中体现为:“恭”与“宽”。“恭”是孔子要求为人处世应有的一种端庄、严肃、彬彬有礼的仪容态度。
孔子认为,一个人做到了“居处恭”、“貌思恭”、“执事敬”、“行笃敬”、“祭思敬”、“修己以敬”,就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故曰:“恭则不侮。”“宽”要求为人处世要宽容厚道。宽容别人, 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宽,意味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为人宽容厚道,就会得众而不孤,故云“宽则得众”。“爱”,是人与人之间善意的情感与心理状态,只有自己首先给予别人“爱”,做到“爱人”,才能收获别人的“爱”,长此以往,才能建立自尊的心态。“仁”与“爱”作为自尊心态的情感基础,在孔子思想中起根本基石之用。
2 智与明是自尊心态的理性方法
《论语》中“知”与“智”同形,其中读“智”者有24处,全为名词,与“愚”字相对,有聪明、智慧、明通等义。“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里“智”和“仁”、“勇”相并列,成为“君子”的“三达德”之一。孔门的“诲人”宗旨,在于使其成为“君子”,所以孔子以“智”诲弟子,弟子亦以“智”问孔子。《颜渊》篇记樊迟“问智”,孔子答以“知人”即是明证,是指明辨是非善恶、真伪的素养与认识能力。孔子认为:“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重“仁”亦尚“智”,故常将“知”(通智)与“仁”并言。如云:“知者不惑,仁者不忧。”“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无私的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德性;“智”是一种判别是非曲直的能力。智者达于事理,周流无滞,像水一样圆通而神,故其“乐水”。仁者安于义理,厚重不迁,像山一样方能稳重,故其“乐山”。智者动而不滞故快乐,仁者静而有常故长寿。仁者以“仁”为内在目的,故安其仁而不迁;智者以行仁为手段,故利其仁而不倦。二者体道虽有深浅之不同,但智者利仁不倦,久之转智成德,自可进达于“安仁”之境。《论语》中没有明确提出“明”字,但通过“自省”得以体现,即“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是自我意识能动性的表现,是形成自尊心态的理性方法之一。以心态视角分析,自省是一种能力,自省能力好的人表现为意志力强、个性独立并有自己内在世界观而且显得有自信。一个人一旦拥有了智慧,并拥有了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就等于掌握了自尊心态的形成方法。故而“智”与“明”是形成自尊心态的很好的理性方法。
3 义与礼是自尊心态的价值准则
对于“义”,孔子明确提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以义作为一种价值标准,进而生成自尊的心态。且这种价值准则,并非外在的戒律或强制,而是人心中固有的观念,孔子肯定物质生活的必要性及合理性,追求合乎道义的物质生活,但更注重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提倡人的道德精神追求应高于人的物质生活追求,这正是自尊心态所需的一种准则。孔子强调的“礼”乃是义的贯彻,他所重视的就是包含于礼之中的道德价值准则。“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可知“义”与“礼”是质与行的关系。“义以为质”,说明“义”是“礼”的实质、本质;“礼以行之”,是说“礼”为“义”的外显,即循礼而行,“礼”是“义”的具体规范与行为模式。“礼”对个体的外部行为方式有着颇为繁复的规定,被孔子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是立人之本,“不学礼,无以立”。“礼”之所以称为立人的根据,就在于它起调节心态之功用,生成自尊心,从而教人们怎样去做一个符合社会所期望的人。“礼”不仅规定了社会结构和秩序中各个角色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还详细规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行为规范,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准则。在孔子看来,立于礼,就是使自己内心符合于礼的要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自我把一切言行举止必须全部纳入礼的规定中,意味着礼成了强制性的绝对命令,以此才能自觉努力地承担并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所谓“礼之用,和为贵”,礼的社会作用就在于使人们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以一种价值准则生成自尊的心态,进而形成良好的道德关系与和谐的社会秩序。
4 学与行是自尊心态的实践模式
自尊要通过学习并实践的模式得以实现。在学习中获得知识、增长能力、丰富自我、心胸豁达,不仅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更可以培养自尊心。在“行”即实践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地理解自尊、实践自尊。孔子以“好学”自命,“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好学’在《论语》里是对一个人非常高的评价。”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只有颜渊被称为“好学”。有人问孔子,你弟子里面有没有好学者?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也强调“博学”和“多学”,“它包括实践和认知两个方面,都是精神的训练。学习不仅要用‘心’,而且要用‘身。有曾子自省为例:“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样的学习,既开启思想,又锻炼身体。正如“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所示,身与心两方面的训练都需要,且学和思互补。仅仅学习不足以达成自尊,且需真正的实践。孔子非常重视“行”,提倡“躬行君子”。主张听言观行:“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也就是说,评价一个人是否拥有自尊,不能仅凭其言谈,而要看其行为,要看他是否言行一致。在知行关系上,孔子强调“行”即道德实践的优先地位,认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入孝悌,泛爱亲仁的道德践履活动重于并先于“学文”的认知活动。道德并非空谈虚文,它首先需具备实际的行动。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谨慎守信、爱人亲仁,这些都是有实际的表现,行有余力才去学文。“闲闲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自尊心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人在行为中现实地表达了对客体的价值判断,获得对客体的价值认识。自尊的实质在于行,而不在于知,它是行得,而不是学得。学得再多,不能见之于行,也不能称为有自尊,相反,它只表示了虚伪和无德。孔子主张“言之必可行”,反对言行不一,“言而过其行”。经过学与行的结合,就等于践行了自尊的心态。“在现实生活中,孔子屡屡遭挫,因而不得不多方面调试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调试就是达成自尊心态的过程。由此,透过《论语》可知在孔子的思想中,注重自尊心态的培育,以“仁”与“爱”为情感基础;以“智”与“明”为理性方法;以“义”与“礼”为价值准则;以“学”与“行”为实践模式,这些皆为自尊心态的实现作铺垫,进而为当今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供精神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