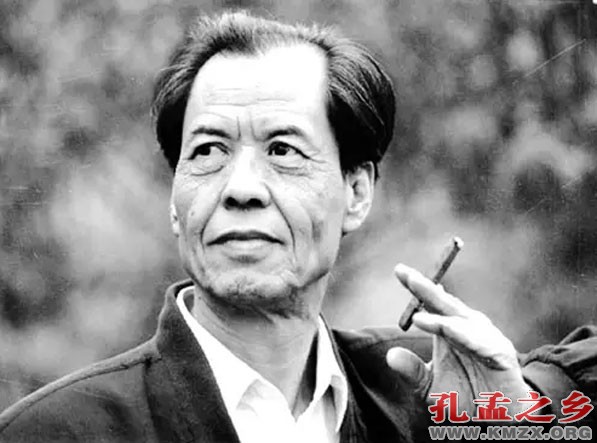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白鹿原》,首先在《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其后它的单行本于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白鹿原》在1992年与1993年之交的出现,就像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中突然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格外引人注目。从那时到现在,《白鹿原》固然是备受赞赏,备享美荣,然而这期间,既有不客气的批评,更有蛮横的政治压制,有那么一段时间,竟然不允许公开发表宣传、评介《白鹿原》的文字,仿佛让它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似的。
人文社派编辑去西安看稿
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1942年生于西安市东郊浦桥区的蒋村。1962年毕业于西安市三十四中学,以后曾担任过农村中小学教师,从事过基层文化工作。196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9年加人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为陕西省作协的专业作家。196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现为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年轻时,陈忠实便很崇拜柳青,在文学创作特别是语言运用上也刻意模仿学习柳青,以致有“小柳青”之称。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完成了《康家小院》、《初夏》、《蓝袍先生》等八部中篇小说、八十多篇短篇小说和五十多篇报告文学作品之后,他不但对以前的创作感到不满,而且也认识到“一个长到十岁的正常的孩子还牵着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议的”(引自《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因而自觉地要摆脱柳青的影响,以求真正的创新并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个性。
小说《白鹿原》的艺术构思即在这种背景下完成于1987年。这期间,作者又在西安平原的蓝田、长安、咸宁三个县做了较深人的人文调查,同时做了其他文学、史学和艺术上的准备,才在1988年4月动笔。这时,陈忠实已认识到:“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而他的创作,只“不过是竭尽截止到1987年时的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关于(白鹿原>的答问》,载《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这样,《白鹿原》终于在1989年1月完成初稿,又经过反复琢磨、修改,在1992年1月完成二稿,并于同年3月改定。从构思到定稿历时近五年。
1973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当时的小说北组便分管西北片,即曾热情地向柳青、杜鹏程、李若冰等人和当时还相对年轻的路遥、陈忠实等陕西作家组稿;1981年调到《当代》杂志,又分工管西北、西南,陕西当然还是工作重点。尽管这中间当援藏教师(1974~1976年)和参加《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1976~1980年)使我和当代创作界的联系,有过六七年的中断,但和忠实以及西安的作家们的交谊并没有中止。1984年,我在《当代》编发过他的中篇小说《初夏》(载该年《当代》第4期头条,被评论界认定为忠实的代表作之一,获本年度《当代》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到1992年,我和忠实的交往、友谊已有20年了。
1992年早春,我高兴地收到忠实给我(时任《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的来信。忠实在信里谈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情况,他说他很看重这部作品,也很看重《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态度,在我们表态之前,他不会把这部小说交给别的杂志社和出版社,希望我们尽快派人去看稿。我把忠实的来信交给当时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朱盛昌等同志传阅。我们商量后决定派《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和人文社当代文学一编室(主管长篇小说书稿)的负责人高贤均一道去看稿。这是在1992年3月底。高、洪二位在返程经过成都时开始看这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一看就放不下,就拍案叫好,并轮换着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就看完了。等他们回到出版社,我们便按三级审稿制由《当代》杂志和当代文学一编室好几个同志流水作业地快速看完。
这样,从1992年4月至6月,《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常振家和我先后完成了对这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的三级审读,实际主持工作的人文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副主编朱盛昌也在8月上旬签署了同意按我的意见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此稿的意见。几乎同时,人文社一编室也完成了对《白鹿原》书稿的审读程序,并于1992年年底正式发稿,在1993年6月正式出书。
实际上,我们当初把《白鹿原》看作很严肃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把它当作畅销书,所以初版只印了14850册,稿费也只按千字几十元付酬。到盗印本蜂起,我们才手忙脚乱地加印,到同年10月已进入第七次印刷,共印56万多册;为维护作者的权益,也才主动重订合同,按最高标准的10%版税付酬。此后,作为雅俗共赏的常销书,《白鹿原》每年都要加印,迄今印数已达977850册(含修订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优秀中国图书书系和精装本)。陈忠实自己的直接调查显示,《白鹿原》的盗印本不下十种,而其印数则与正版接近。(陈忠实:《从盗书到盗名》,载2000年12月20日《中华读书报》)如此看来,说《白鹿原》的实际总印数迄今已在200万册以上,当不为过。
作家陈忠实
内部审读,《白鹿原》被一致看好
《白鹿原》在内部审读过程中几乎被一致看好。当然,编辑在看稿的过程中,心里不但有作者、读者,而且还会有上级领导,有相关的政策管着。因而,他们不但看到了、充分肯定了《白鹿原》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魅力,而且也注意到了它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可能引起责难的地方。
下面,让我们不惮烦地摘引有关的审读意见,以一窥当时编辑部内部对《白鹿原》的高度评价和有关的思考。
(一)《当代》杂志审读意见
洪清波的初审意见(1992年4月18日):
作品最突出的优点是,所描写的生活非常扎实,因而就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当代文学创作中,如此生动、丰富、真实描写农村生活的还不多见。
其次,人物形象非常成功。白嘉轩、鹿子霖是两家的家长,他们的命运无不与历史许多重大事件相关,所以他们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缩影。用既定的思想观点很难判断他们一生的是是非非,但是读者无法怀疑他们的真实性。
在艺术表现上,总的看来十分朴素。作品以叙述为主。一般说来叙述得比较清楚,并显示出一定的丰富性,但也有个别地方有枝蔓(和)不合理的问题。当然,作为一部长篇,这种朴素的表现方式,显得有些单调,特别是有时候该出情绪的地方,烘托不上气氛。但是这也与作者的写作风格、描写内容有关。此作是比较冷静的现实主义,很少渲染夸张。
总之,此作可读性较强,内容丰富,认识深刻,我以为是很不错的作品。
常振家的复审意见(1992年5月3日):
这是近年来一部比较扎实的作品,历史感强,人物形象鲜明而丰满。特别是作者能把人物的命运与性格的展示同整个社会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这就不仅加强了人物性格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而且使作品产生一种厚重感。
作品不足之处在于笔墨过于均匀,变化较少,“浓淡相宜”注意不够。有些性的描写似应虚一些。但总的来说,这还是一部不错的作品。
何启治的终审意见(1992年6月30日):
这是一部扎实、丰富,既有可读性又有历史深度的长篇小说,是既有认识价值也有审美价值的好作品。
1.此作体现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历史观、革命观。在政治上是反“左”的,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思想路线(实享求是)的。写国民革命、写国共又合作又斗争的历史相当冷静、准确、可信。可以说比较形象、真实地描绘了国共两党初期闹革命阶段的真实面貌,如十六章写白灵、鹿兆海以铜元的正反定入党的对象,其后又在实践中互变为另一党的党员,就很有时代特色。
2.此作通过白、鹿两个家族、两代人的复杂纠葛反映国民革命到解放这一时期西安平原的中国农村面貌,也是准确而有深度的。我们有一个时期以简单的阶级斗争(甚至扩大化)观点来统帅一切,事实已证明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白鹿原》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作者的冷静和勇气,而作为文学作品,则显得既新鲜又深刻、准确,因而特别值得肯定,值得重视。
3.作品的历史观和革命观都不是概念的表述,而是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塑造和生动、形象的生活画面来表现的。
如老一代的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就写得很好。朱先生作为一个有骨气的正直博学的知识分子写得很成功。白嘉轩作为一个有原则且能身体力行的倔强的族长形象也很动人。十六章写他被打断了腰仍不失威仪,夺过鹿三的牛鞭子在夕阳中扶犁耕地,就像一幅充满悲壮意味的夕照图。鹿子霖干尽了坏事,但也不是简单地(写他)干坏事,都按一定的生活逻辑落笔。凡此,显示了作者的冷竣和艺术工力。(长工鹿三的形象也值得注意)
当然,鹿兆鹏、鹿兆海兄弟和白灵、白孝文、黑娃等形象也不错。特别是小娥这个表面看似淫荡而实际上并未泯灭人性的艺术形象也是成功的,值得注意的。
这就牵涉到此稿的性描写如何处理的问题。首先,我赞成此类描写应有所节制,或把过于直露的性描写化为虚写,淡化。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性描写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一定就是丑恶的、色情的。关键是:应为情节发展所需要,应对人物性格刻画有利,还应对表现人物的文明层次有用。自然,应避免粗俗、直撼。试想,如果《静静的顿河》去掉了阿克西妮亚会成个什么东西?如果《子夜》删掉了冯云卿送女儿给赵伯韬试图以美人计刺探经济情报这段情节,又怎么样?(这情节不但写活了赵伯韬的狂傲,冯云卿的卑鄙,也写出了冯女的幼稚和开放。)《白鹿原》的小娥就是个很重要的形象。她在鹿子霖挑唆下拉白孝文下水这一段性情节,就很能表现鹿子霖的卑鄙,白嘉轩的正直、严厉以及小娥和白孝文的幼稚和基本人性、为人态度等等,是不可少的情节。
此外,作品还有一些比较弱的或比较经不起推敲的部分(如992页写白灵发动学潮,1218页鹿兆鹏让鹿兆海送白灵到张村,1427页反反复复讲白孝文买鹿家门楼等等),应在编辑时或删或作适当改动处理。
陈忠实迄今最重要、最成功的小说就是这一部……赞成适当删节后采用,刊《当代》今年第6期和明年第l期。请发稿编辑把文字加工工作做细一些。(大约可删去五万字左右?)
朱盛昌(时任人文社副总编辑,实际主持《当代》杂志工作)意见(1992年8月10日):
按何启治同志的意见处理。
关于性描写,我不是反对一般的两性关系描写。对于能突出、能表现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发展所需要的两性关系的描写是应当保留的。但直接性行为、性动作的详细描写不属此例,应当坚决删去,猥亵的、刺激的、低俗的性描写应当删去,不应保留“……不要因小失大。
(二)当代文学一编室意见
刘会军的初审意见(1992年12月18日):
这部作品既有严肃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生动引人入胜的故本情节。两者完美的结合,提高了小说的品位。它对生活的冷峭、深邃的描写,对人物琢磨不定,但又入情合理的性格刻画和总是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以及篇幅宏大而情节、人物单线发展却又完整自然的框架式的艺术结构,都显示出作品的独到之处。它既能引起作家、出版家、评论家、学术研究者的重视,也能受到一般文学爱好者的喜欢,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它的经济效益在目前情况下不敢企盼过高,但希望在文学评奖中获奖,还是抱有信心的。
#p#副标题#e#高贤均的复审意见(1993年1月11日):
同意刘会军同志的评价和估计。采用这部书稿主要侧重在它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一部好书迟早会得到社会和读者的重视。基于这点,我们对它的经济效益也是有信心的。
何启治(1992年9月调任人文社副总编辑,分管当代文学的出书工作)的终审意见(1993年1月18日):
同意初、复审对《白鹿原》的基本评价。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
《白鹿原》就这样在《当代》和人文社编辑们的赞赏关注之下走向社会,走向读者。而有心人在读过上引审稿意见之后,也当更能体察《白鹿原》诞生时所处的气候、土壤和环境等条件。
“洛阳纸贵”,却被禁止宣传
《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说明“洛阳纸贵”的一个小例子是:人文社前总编辑屠岸曾应音乐家瞿希贤的要求为他寻找《白鹿原》的下半部。原来,瞿的女儿在法国学美术,一批海外读者在《当代》1992年第6期看到《白鹿原》的上半部后,便迫不及待地寻找它的下半部。
还有人记述1993年盛夏某日,陈忠实在西安市北大街省新华书店为《白鹿原》签名售书的盛况。从清晨6时到烈日当空的中午,西安市和从咸阳、铜川、临渡、宝鸡等地赶来的读者排成了长队。甚至还有从北京到西安出差的人,也加人了等候签名售书的队伍。向陈忠实致敬的读者,不但有送红玫瑰的大小伙子,还有送上两把梳子,并说明如何使用梳子才有益大脑的理发师。此情此景,着实令人感动。(见1993年11月15日《香港作家》七版郑文华文)
在前辈评论家中,朱寨指出:“《白鹿原》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凝重。全书写得深沉而凝练,酣畅而严谨。就作品生活内容的厚重和思想力度来说,可谓扛鼎之作,其艺术上杼轴针黹的细密又如织锦。”(见《<白鹿原)评论集》第40页)
张锲说:“《白鹿原》给了我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阅读快感和享受。”有“初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楼梦》时那种感觉”。(见1993年7月16日《白鹿原》北京讨论会纪要,转引自(《白鹿原>评论集》第432页)
范曾读《白鹿原》后即赋七律一首:“白鹿灵辞渭水破,荒原陌上维宗祠。族旗五色尧成华,史倒千秋智变痴。仰首青天人去后,镇身危塔蛾飞时。奇书一卷非春梦,浩叹翻为酒漏危。”并附言:“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甲戌秋余于巴黎读之,感极悲生,不能自已,夜半披衣吟出七律一首,所谓天涯知己斯足证矣。”(据范曾赠《白鹿原》作者手迹)
还有海外评论者梁亮也十分激赏地指出:“由作品的深度与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见《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杂志1994年第14期)
……此类事例,真是不胜枚举,还是就此打住吧。
然而,我们已经注意到,自《白鹿原》问世以来,就在好评如潮之外另有一种不同的声音。例如,朱伟就在他的《<白鹿原>:史诗的空洞》一文中说:“这部《白鹿原》使陈忠实丧失了自己。”然后慨叹:“一部使艺术家丧失了自己的作品,被捧上了那样的高位,这难道不是中国文学的悲哀吗?”张颐武则在《<白鹿原>:断裂的挣扎》中表示惋惜说:“《白鹿原》却仅仅是一个断裂处挣扎的文化产品。陈忠实的卓绝的努力和虔诚的创作态度并未结出理想的果实。”孟繁华也认为,《白鹿原》不过是引领着读者在已往的“隐秘岁月”里,作了一次“伪`历史之旅”,—即“消闲之旅”而已。(上引三文均见于《文艺争鸣》杂志1993年第6期)
如果说,上述言论只是文艺圈内的不同意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属正常的学术性争鸣的话,另外有些现象就让人深感压抑而又无奈了。
从1992年到1999年,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辑和《白鹿原》一书的终审人以及责编之一,我从来没有见到上级领导关于《白鹿原》的任何结论性的指示,书面的固然没有,连电话通知也没有。书照样重印着,照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却就是不让宣传。
1993年7月,《白鹿原》出书后一个多月,专家和读者反应都很热烈。我理所当然地组织一些评论家写文章,并将朱寨的《评<白鹿原>》和蔡葵的《<白鹿原>:史之诗》两篇短文送首都某大报。清样都排好了,就要见报了,到后来却还是被退了回来。编者无奈地表示:反正有人不让讨论《白鹿原》,所以肯定它的和批评它的文章都不好发(这两篇文章现均收人2000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鹿原>评论集》中,已经是在报纸禁发七年之后了。)
这种状况到了1997年还没有好转。这年5月,在天津开会评“八五”(1991~1995年)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时,我以评委的身份联合另外两位评委(雷达、林为进)建议把《白鹿原》列人候选作品的名单中,却意外地受到临时主持人的粗暴干预。我也由此明白,在那时候,在有关领导机关某些官员的心目中,长篇小说《白鹿原》竟是连评奖候选的资格都没有的。
就这样,不管读者怎么喜欢,不管文艺评论界如何赞赏,《白鹿原》在长篇小说评奖活动中却连候选的资格都没有,在报纸上也不让宣传,真是如同被晾在无物之阵里,令人深感压抑而又无奈。后来,我从一个在新闻界工作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原来是某领导机关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什么会上说了批评《白鹿原》,不要再宣传《白鹿原》的话。这样,就真的把《白鹿原》晾起来了。不管什么正式场合和活动,《白鹿原》竟成了敏感的、可能招祸的、不能碰的话题了。
和这种暗地里的压制不同,某业务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倒是很直白地公开说出了他对《白鹿原》的看法。他说,写历史不能老是重复于揭伤疤。“《白鹿原》和《废都》一样,写作的着眼点不对。”并指出,“这两部作品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片,变成画面展示给观众。”(见1993年12月13日《羊城晚报》转引《金陵晚报》常朝晖文)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只是简单粗暴也一目了然。这种公开的表态,也让人明白了:原来这些年对《白鹿原》的不公平待遇都是事出有因啊。
陈忠实近照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白鹿原》在具官方色彩评奖中均告落选
现在,再让我们看一看《白鹿原》诞生以来在各种评奖活动中的情况。
1998年7月,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组在无锡组织了一次活动,其中一个内容是由与会嘉宾举出20年来自己最看重的一部书并略述理由,作为对新时期以来优秀出版物的肯定和回顾。当主持人李潘把话筒交给我时,我毫不犹豫地说,“作为一个文学老编辑,20年来我最看重的一部书就是陈忠实著长篇小说《白鹿原》,理由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
我想,这也可以看作我个人参加的一次优秀图书评选活动吧。但当时就有与会的朋友说,你对《白鹿原》这么敏感的话题这样表态,恐怕未必能通得过,公开播出这个节目时你的话很可能会给剪掉`我对这位好心朋友的看法能够理解,而私下里却以为,也不一定就会把我的话剪掉,如果照放,那就说明我的认识在相当层次上还有知音呢!
果然,这个节目正式播放时,我的话并没有被删掉。为此,我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然而,《白鹿原》诞生以来,在正式的相关评奖活动中,却只在民间组织的评奖活动中得到肯定:
1993年6月10日,《白鹿原》获陕西省作协组织的第二届“双五”最佳文学奖。
1994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一批资深编辑组成的评委会通过认真讨论和无记名投票,一致同意授予《白鹿原》以“炎黄杯”人民文学奖(评奖范围为1986~1994年人文社出版的长篇小说)。
除上述两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白鹿原》在比较具有官方色彩的评奖(例如“国家图书奖”)活动中,均告落选。如前所述,在“八五”(1991~1995年)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的评选活动中,它连候选的资格都被粗暴地勾销了。
那么,在文坛瞩目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议中,《白鹿原》的境遇如何呢?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议从1995年起动,到1997年12月19日揭晓,历时两年多,可见其中的复杂和艰难。
《白鹿原》先在23人专家审读小组(读书班)顺利通过,却在评委会的评议中出现不小的分歧,以致评委会负责人在评议过程中不得不打电话给陈忠实,转达了一些评委要求作者进行修订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见《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第152期“本报讯”)对评委会负责人转达的上述修订意见,陈忠实表示,他本来就准备对《白鹿原》作适当修订,本来就意识到这些需要修改的地方。于是,忠实又一次躲到西安市郊一个安静的地方,平心静气地对书稿进行修订:一些与情节和人物性格刻画没多大关系的、较直露的性行为的描写被删去了,如删去了田小娥第一次把黑娃拉上炕的有一些性动作过程的描写,关于国共两党“翻鏊子”的政治上可能引起误读的几个地方或者删除,或者加上了倾向性较鲜明的文字……总共不过删改两三千字的修订稿于1997年11月底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本于12月出书。
据说,在评委会对《白鹿原》的评价出现明显分歧时,老评论家陈海对它的肯定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在他看来,“陈忠实从他70年代发表小说开始,便一直是一个接续过去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他还很少受到其他艺术方法的影响。”而《白鹿原》则让我们看到,陈忠实“充分地理解现实斗争的复杂性,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这个特点,但又同样清楚地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尽管陈忠实在自己探索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斗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自己主观认识上的一些问题,但他整体思想倾向的正确是应该肯定的,他的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解放前中国的现实的真实,是主要的。”(转引自《<白鹿原>评论集》第119、227页)
无疑,陈海对《白鹿原》的肯定对它的获奖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陈忠实本人适当的妥协和对《白鹿原》所作的并非伤筋动骨的修订,对它的获奖当然也是重要的。
就这样,长篇小说《白鹿原)}(修订本)终于榜上有名,荣获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第四届)。1998年4月20日,它的作者陈忠实终于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台。
颁奖大会后,中央电视台在对我的采访中问我如何看待《白鹿原》的获奖。
我当即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作为《白鹿原》的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我要负责任地说,《白鹿原》的修订并不是如有些人所顾虑的,是“伤筋动骨”而至于“面目全非”。牡丹终究还是牡丹。修订过的《白鹿原》不过是去掉了枝叶上的一点瑕疵,而牡丹的华贵、价值和富丽却丝毫无损。
#p#副标题#e#第二,如果我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我会痛痛快快地给《白鹿原》投上一票,而不会要求对它进行修订。因为《白鹿原》在深刻思想内涵和丰厚审美意蕴上的出类拔萃是不容否定的客观存在。至于作品的缺点,那是世界文学名著在所难免,是改不胜改的。
第三,如果《白鹿原》的作者只有作适当的妥协才能使它获得茅盾文学奖,那么,我是理解并支持作者作适当的妥协的。因为《白鹿原》获得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之最高荣誉,对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有利,对发展整个当代文学有利—《白鹿原》能够蹚过去的地方,其他文学作品也应该能够蹚过去。因此,我对《白鹿原》(修订本)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殊荣表示由衷的祝贺。
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爱戴、拥护、崇仰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堪称为“大书”的优秀作品,而不知呵护、赞赏和热爱的民族,也同样是可悲的。
幸而,想非难甚至压制《白鹿原》的毕竟是很少数人。
幸而,《白鹿原》不但获得了“双五”最佳文学奖和“炎黄杯”人民文学奖,而且最终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殊荣,真是让人感到欣慰。
然而,《白鹿原》从1992年与1993年之交诞生,我们直到今天才能比较从容地、坦然自信地来回顾《白鹿原》诞生以来的是是非非,这中间,难道不是颇有一些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么!
何启治
广东龙川人。中共党员。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中宣部山西文化工作队队员,西藏格尔木中学援藏教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当代》杂志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中直工作委员会委员。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天亮之前》(合作),评论集《美的探索》(合作),散文报告文学集《梦·菩萨·十五的月亮》等。纪实文学《中国教授闯纽约》获中国505杯报告文学提名奖,传记故事《少年鲁迅的故事》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纪实文学《播鲁迅精神之火》(合作)获中国作协优秀报告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