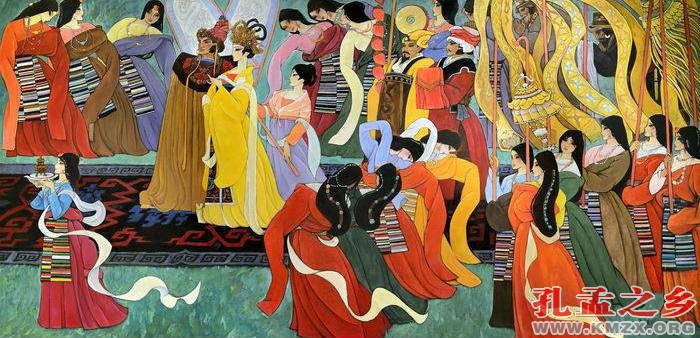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婚姻佳话,已成为汉藏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此,《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都有记述,《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贞观15年(公元641年)春正月……丁丑,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从这寥寥数语中,我们可以知道松赞干布向江夏王李道宗是行的“子婿礼”,道宗当然就是文成公主的父亲了。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叔伯兄弟,李道宗是刚刚被封为江夏王,此前却是当了近二十年的任城王,而任城就是当今的山东济宁。文成公主出生、生长于任城当是确切的了。
任城——长安——拉萨,她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孔孟之乡,当然走红的是圣人,何况还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圣训,即使贵为公主,也因其是女子而连个名字也没能留下来,并且长久地被生养之地忘记。一千三百二十多年来,我们即便想起她,也仅仅是把她当作“和亲”的工具;赞美着,也只是赞美她为“政治”所作出的贡献。至于一个女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个女人丰富多采的情感世界和她那无处倾诉的心里历程,一个女人的苦难与牺牲、孤独与忧伤、需要与思念,谁还会顾及呢?
但是,有时越被忽视的却越是不朽。在我国西藏,问孔子,肯定有好多人不知道。要是问孔子的老乡文成公主,几乎是没有不知道的。虽然她连个名字也没留下,各种皇家官方的史书上,也对她的生平事迹忽略阙如,可是她的音容笑貌,却早已融入于西藏高原的山山水水和世代藏族人民的心上了。有千年不化的冰川雪山,有四季清冽的雅鲁藏布江,青藏高原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巨大的保鲜库。它不仅保鲜着原生状态的大自然,也保鲜着纯美博大的情怀。让我们尝试着走进她的世界,问候她,也去理解她——
成婚之路,其实就是不归之路。一个大唐女子,所要承受的不仅是和家乡、父母、亲友以及共同营造起的温暖生活的永别;她要从公元641年一直跋涉到643年,才能走完她的艰险的成婚之路;尔后,她更要只身面对一片洪荒寒冷的莽原、一个语言不通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还有难耐的缺氧、寒冷、孤单与迥异的生活环境。
李世民到底是个富有人情味的皇帝。即皇帝位的当月他就解放了三千多名宫女,并于第二年(贞观元年)二月下达了让黎民百姓成亲的诏书,要求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没有成亲的,州县政府要“以礼聘娶”;家里贫寒没法成亲的,“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还细致地要求,对于六十岁以上的鳏夫、五十岁以上的寡妇和愿意守节的妇女,不能勉强。能够体察民瘼的李世民,对于皇亲国戚当然更加疼爱有加了,所以吐蕃的松赞干布多次求婚都被他拒绝了。他不忍让亲骨肉生离死别。谁知强悍有力、统一了西藏的松赞干布硬是倾慕大唐公主,宁可开战也要成婚。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毕竟要以江山为重,踌蹰再三还是应下了这门亲事,“妻以文成公主”。李世民有二十一个闺女,可他扒拉来扒拉去,哪个也不舍得放到如此荒凉的地方去,也许他私下里征求过意见,就是没谁愿意去。没法,只好封个叔伯兄弟的女儿为公主嫁过去吧。
这是绝对不能违抗的圣旨。正月,西秦之地的长安够冷的了。文成公主却要随父亲走向更加寒冷的西域,而且没谁注意到,公主丰腴端庄的容颜下,会藏着丝丝惆怅,还有些许恐惧。我们不能期望十八九岁的花季,会有一个政治家森严深奥的胸襟。是幸福还是灾难,是盛开还是枯萎?在公主的担心与期待里,大唐送亲的人马一路向西,向西;而在遥远的西域,正有由松赞干布率领的迎亲的队伍,浩荡着一路向东,向东。山脉连着山脉,荒漠连着荒漠,没有人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的风雪裹挟着娇嫩的公主和公主那浓浓的愁绪。这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长、最险的成婚之路了。已经变为枯骨的王昭君,也会在地下为文成公主的千难万险而深深叹息吧?冬天尽了,春天到了,向西、向东的队伍还在不懈地跋涉着,连风雪也没有停歇的意思。等到终于在青海的鄂陵湖、札陵湖畔相逢的时候,已是第二年初夏的季节。当家乡在艰辛的熬煎里一步步远去的时候,一个全新广袤的天地也在一点点真切地进入到她的心里,那爿能够包容世事、消解苦寒、慈爱仁厚的女性的情怀,也便一日日成熟丰饶起来。
举手送别一步三回首的父亲,强忍着的泪水终于还是小溪般地夺眶而出了,只有满月似的脸庞上还透着坚强与安祥。她那成熟丰饶的情怀明镜似的知道:这是永诀,又是开始;是埋葬,更是新生。
相逢的刹那,有一缕喜悦便迅疾地飘过她安恬而略带忧郁的眼睛,还有兴奋的红晕悄然照亮了她那矜持的神态——松赞干布,本意为一个伟大、正义、博学的人,二十五岁的松赞干布所给予文成公主的第一印象,正是这样一个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在他十三岁上,代表了保守贵族利益的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发动了叛乱,并将统一了西藏的父王论赞弄囊毒死;十六岁的时候,他就以一个英雄的胆魄一举平定了叛乱,毅然迁都逻些(今拉萨),并在其后的十年间创造了西藏历史上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与这样一个男子生死相守,该是一个女子千载难遇的福分啊。公主甚至在内心深处涌起了为他做一个好女人的冲动。况且,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直觉,让她清楚地感到了这位吐蕃王对自己的喜欢与钟情。雍容华贵、风情万千、知书达理、宅心仁厚的大唐公主的力量,是胜过千军万马的。爱的灵犀便在无言中相通了。
望着为了自己专门穿上汉族袍带的松赞干布,望着前方的这块无限辽阔的高原,她那曾经凄楚不定的心情一下安宁下来,并默然做出了以命相许、吐蕃为家的终生不渝的誓言。
还有什么诺言能比一个女子以命相许的誓言更为珍贵、更为重大、也更为真实呢?因为她们是以无私、博大而又持久的爱去践诺的。
强烈的高原反映,加上对亲人与故乡的思念,文成公主曾经度过了无数个失眠之夜。她总常常想起开放的、胸襟阔达的大唐帝国,想起能征惯战而又充满着治国智慧的太宗皇帝,想起英勇善战、博学多识的父王,想起怡怡相亲的母亲与兄弟姊妹。但是,越是想起这些,她便越发地热爱着身旁的这位英雄、热爱着他们共同拥有的吐蕃王国。谁说他和这方无垠的高原是落后、封闭与野蛮呢?她的男人有着高原一样宽阔的胸怀和雅鲁藏布江一样开放的性格——他派贵族子弟留学天竺,并创造出了藏族文字;他聘请了泥婆罗的手工技师、天竺的学者、大食的医生;他更留意学习大唐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她的出嫁,不就是应夫君的请求,带着乐队、工匠、技师、学者,带着种子、工具,带着大宗的有关经史、佛经、诗文、种树、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来的吗?他不仅精通骑射、角力、击剑、布阵,而且擅长吟诗,熟记各种英雄的传说,并能唱一口雄浑嘹亮的民歌。还有粗犷纯朴、虽罹无穷的苦难仍然情深谊重的人民,还有凸兀静穆的雪山和无比清冽圣洁的湖泊与江河,还有烈如波涛的野马野驴和如泣如诉的驼铃……她的爱怎能不与雪山共高与江河齐舞呢?他们、尤其是公主,早已跨过了“和亲”与“甥舅之盟”的政治的界线,而让一种渗入骨髓而又绵亘不尽的人生之爱在高原上弥漫开来。有了爱的滋补,英武剽悍的松赞干布,明显的柔和起来,广大藏族人民也更多地得到了他的体贴与关怀。甚至他在险恶的政治风云与战火的磨砺下所生长起的猜忌与残忍,也在这种爱的抚慰中消融了。就连高原的冰川雪山,也因其而富有了柔情,沐浴着温熙的太阳。
爱,是她带给松赞干布和他的吐蕃王国的最为珍贵的奉献。爱,也是她背井离乡永别亲人后的最为重大的人生收获。
但是,播种或收获巨大的人间之爱的人,注定要经受非同常人的磨难与考验。公元650年,年仅三十四岁的松赞干布病逝,一下子将文成公主抛进痛苦的深渊!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当年文成公主的哀伤与创痛。正值盛年,失去挚爱的人,又没有一个同胞亲人在身边劝慰,该有怎样的力量才能度过未来的时日?她不在乎地位与荣耀,甚至也不需要青史留名,她是一个女人,她只要那个相知相爱的男子汉,只要那个充满炽热的情爱、可依可靠的忠诚的胸膛。但是这一切骤然离她而去,在她以为来日方长的时候骤然离她而去。永远失去故乡与家人之后,她又永远地失去了唯一的爱人。
她没有让哀伤击倒。文成公主再一次证明了:女人注定要承受更多的苦难,女人注定能承受更多的苦难;女人因为承受苦难而美丽,女人也因为承受苦难而伟大。她不仅跨过了失去丈夫的深渊,而且又在丈夫所挚爱的土地上整整生活了三十年,直到公元680年10月丙午,才怀着对于吐蕃和吐蕃人民无限的留恋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不是“熬”过的三十年,她是在爱的升华与生命的升华中度过了三十年意义非凡的岁月。而对于佛的皈依与契合,则是这种升华的肯綮。只有佛的博大无垠,才能放得下她的思念,她的情感,她的痛苦,她的欢乐;也是佛的慈悲,不断地拓展着、丰富着她那贤慧聪颖的女性情怀。在这三十年的人生岁月里,她对丈夫的爱生长得更加深长起来,并把这种深长的热爱,点点滴滴化作对于这方土地和对于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的热爱与帮助。她以一个女性特有细腻,体察着吐蕃人民的苦难与需要,敏悟到在政治与物质之外,人民还需要精神的依归与抚慰。而越是苦难的地方,越是佛性生长的沃土,因为佛的真谛不是空寂而是悲悯与博爱。于是,她与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一道,共同将融入着自己母爱的佛教的精神在这片年轻而又广阔的大地上传播开来,并开始了一个民族的皈依之路。
她从大唐带去的经书在布达拉宫藏着,她从大唐带去的释迦牟尼像还在大昭寺供着,还有她带去的种子,也在一季又一季的播种着、收获着,而她倾其一生带给这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柔情、温暖和情谊,更是如圣山圣湖一样长在了高原上,长在了世世代代高原人民心灵的殿堂上。一千三百多年过去了,藏族人民至今仍把她当作保护神一样,与松赞干布一起供奉在各个寺庙里。
文成公主不也是人生历史长河中的一盏不灭的明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