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一个观点,说晋陶渊明辞官归隐,是因为清高而看不起污浊的官场,“不为五斗米折腰”,去过他的田园生活,其形象那是相当的“高大上”。真是这样吗?我觉得不然。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最早见于《宋书》“陶潜传”,其中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难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乃即日解印绶去职。”督邮是专门考查县令治绩的官,哪个县令敢得罪?为了能让督邮给自己的治绩打个优良,将来好“更上一层楼”,别说“应束带见之”,请客送礼,百般讨好也是应该的。可是这陶县长却解印绶去职,不要这五斗米了。
五斗米是多少米?缪钺先生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里研究过,说五斗米是当时知识分子一个月的粮食。难道一个县令一个月的薪水及各种“创收”才刚够吃填饱肚子?那谁还去做官。
陶渊明辞官的理由,肯定不是当县令的官职太小、油水太少的缘故。魏晋六朝时代,政府机关行政费用仍然主要依靠自筹,县令因为容易自筹,而中央部门自筹机会较少,虽然中央部门的法定俸禄多于县令,反而出现基层待遇比中央好的情况。所以,很多中央级干部都想调到基层去。比如东晋的王述,是大臣王湛的孙子,宰相王导有心提携,调他到相府工作,孰知他直言孤儿寡母,家境贫寒,要求出任宛陵县令。其后,太尉、司空两府一再调他回中央,实授尚书吏部郎,他一概谢绝。王导托人传话说:“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耳”,他的回答是“足自当止”,要是基层油水不多,他又何必到基层去“揩油”呢?(完颜绍元《官场那些道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8月版)
陶渊明的世身与王述颇为相似,陶的曾祖陶侃为晋朝开国元勋,封为长沙郡公,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但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落。颜延之记载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他自己也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所以,出任县令正应是求之不得的事,何故要辞官不做?
陶渊明处在门阀世族制盛行的时代,做官重门第,士族官僚的把持下官场,庶族寒门的人士很难有做官、晋升的机会。当时的名士李密就曾发出了“朝中无人,不如归田”的感叹。以陶渊明的身世看,他也算是士族出身,“不如归田”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朝中无人”,他能获彭泽令这个肥差,是请托了其叔父走了关系得的,说明朝中关系是相当硬足的。他做了县长之后,生活很快就改善起来,“僮仆欢迎……有酒盈樽”,“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归去来兮辞》),何必在这个时候匆匆辞官而去。
陶渊明辞官历来有多种猜测,比如认为他受“魏晋风度”的影响很深,认为他有贪赃枉法之嫌等等,而我认为,陶渊明辞官主要是官场确实非一般人呆,陶渊明委实不适合在官场里混,并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理由。他在《归去来辞》里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心为形役”四字点破了他辞官的主要理由,也道出他自知之明,所以一走了之,但并不能说明他清高到不为五斗米腰,否则就不会涉足官场,曾经为五斗米折腰。
有些人个性非常适合官场那一套规则,进去以后,溜须拍马,不教自会,如鱼得水,有些人个性极不合宜,左右不是,结果碰得焦头烂额,有的人干脆负气辞官而去,有的人强忍个性熬到退休,陶渊明属于性情不合适最终无法委屈自己那一类,就像朱熹说的,“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此论最精确地揭示了陶渊明辞官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不想做官,而是做不好官;不是不想做个有成绩的官,而是做不出成绩来;不是不想为五斗米折腰,而是想弯腰,但腰生性弯不下来,强弯下来太吃力,只好不吃这碗弯腰的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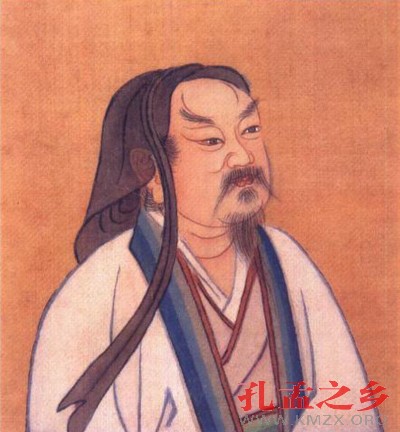
为什么说官场这碗饭非一般人能吃?未曾进入这个围城的人可能不能想象,未曾了解古代官场情况的人也不能想象,要是看看古代官场中人对官场的描写更真实也更服说服力,比如明代的袁宏道,同样是一个县令。
袁宏道是公安(今属湖北)人,“公安派”的领袖,明代最富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家之一,其小品文最为精妙,并且以尺牍大师享誉文坛。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27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县令,初入官场,他感觉风光而体面。但很快就发现官场不是自己能呆的地方,于是不断给友人写信诉苦。
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做官的百般感觉如过山车般滋味一日尝尽。
他在给好友沈凤翔的信中写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当官苦一点也就罢了,还有太多是非风波陷阱,躲不胜躲了,这就非常“难”办了。
他在给同为县令的朋友杨廷筠的信中写道:“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意思是说每天点头哈腰,跪拜逢迎,搞得斯文扫地,身心备受折磨。
当官对于袁宏道来说如此之苦之难之斯文扫地,才做一年的县令,就萌生了去意,辞官之后在给聂化南的信中写道:“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他把辞官归隐比喻成出笼之鸟、脱罟之鱼,放松痛快之心情跃然纸上。
袁宏道笔下的官场就是真实的官场,与陶渊明所面对又有何异?在这里面,你当然可以享受俸禄,衣食无忧,光宗耀祖,优等服务,香车美女,甚至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也可以建立关系人脉,以及占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但是,这此好处是需要某些东西来交换的,这就是你的个性、心灵、人格、自尊,乃至灵魂。它要你把这一切都献给官场和潜规则,与它同流合污,扭曲是与非、黑与白、曲与直,厚得下脸皮,屈意奉迎,吹牛拍马,欺上瞒下;炼就一身驴皮象肉,扛打扛揍,默默忍受;学权谋之术,懂得运用潜规则。
更要紧的是,官场是狼虎成群的地方,要想在官场上混好,内心里得有几份狠劲,骨血里得有几份毒性。你与狼虎朝夕相处,就算不是吞噬别人,也是防备之须,用别人的话说,你手里没有几根象样的打狗棍,怀里没有几斤毒性砒霜,内心里没有三分剧毒,一进到这样的场所,立即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虎狼腹中之物。你只有比别人更狠更毒更坏,才能在官场的逆淘汰中优胜出来。这是一个被“体制化”的过程,至少假装被“体制化”,你才能适应官场,不至被劣币驱逐。在官场里又想要当官的好处得尽,又想能不顺从官场的潜规则,不愿意同流合污、毒招用尽,还企图保持独立之个性、自由之心灵,熊掌和鱼兼得,这是不可能的,官场没有中间路可走,两路必择其一。
陶渊明少时家贫,自然懂得耕种劳作的艰辛,也知道辞官之后生活会贫苦(梁启超说他“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他在官场里几进几出,自然懂得当官的好处和规矩,当他经过不断的尝试来适应官场,却又不断失败之后,才痛下决心与官场彻底决裂,辞官归隐,自谓“误落尘网里,一去三十年。”这期间的心路历程,利弊权衡以及艰难抉择,岂是一般人能体会?要是陶渊明与袁宏道二人能跨越千年的时空聚在一起促膝而谈,一定会彼此视同知己,再次对官场体悟大倒苦水,谈上三天三夜都不够。
有句话叫“性格决写命运”,说得有点绝对了,但“性格影响命运”是肯定的,陶渊明是性情率真,爱好自由的人,这种性情恰与官场发生根本对立,官场不能较真、不能讲自由,没有什么非曲直,也没有什么黑白分明,有的只是勾心斗角,鬼使神差,皮笑肉不笑,陶渊明只能退出竞争而别无他途。简而言之,陶渊明想做官,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耐了很长的性子最后还是耐不住,只好归隐,说到底,陶渊明不是抗议官场,而是逃离官场,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判断陶渊明志行高洁,我认为有些过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