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一名德国的传教士,他将自己的名字镶嵌在青岛的历史中。
卫礼贤原名为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年5月10日出生于斯图加特。在他57年的生命历程中,有20多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以一名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青岛,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1899年,卫礼贤乘船来中国时,他无法预料到将在青岛逐渐完成身份的转变从传教士到汉学家。他更无法预料到自己会拥有一颗“中国心灵”,他的灵魂深深地被中国文化所吸引,学说中国话,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像一块海绵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吸取文化的滋养,成为20世纪享誉全球的汉学家。
卫礼贤在青岛,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崛起,更重要的是,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成了青岛里程碑式的人物。
1900年,卫礼贤在青岛创办了礼贤书院(今青岛九中),这是青岛的第一所新式中学,开风气之先。1904年,卫礼贤建议中德政府联合创办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德华大学,1909年建成)。他组织尊孔文社,弘扬儒家文化,和当时在青岛的文化名流聚会。在他的《中国心灵》一书中有“青岛的故人们”一节,卫礼贤生动地描绘了他与在青岛的劳乃宣、康有为、辜鸿铭、恭亲王溥伟等人的交往。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卫礼贤与清朝的遗老遗少的交往,显示出一幅清末民初的政治画卷。1914年,卫礼贤创建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青岛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亦为中国早期图书馆之一。然而好景不长,日本与德国的战争在青岛这个美丽的城市点燃硝烟,卫礼贤和他在青岛的故人们星散世界各地。
1914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无暇东顾,对德国参战,进攻青岛。卫礼贤的日记记录下日德战争的全过程 。卫礼贤一战期间在青岛的日记,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冷静客观,他虽然是一个德国人,但没有局限在“爱国主义的热情”来记录战事。卫礼贤的伟大就在于此,他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看待眼前发生的战事,以及德国的战败。他的目光看得更加深远 ,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中西文化交流 ,致力于青岛的教育事业。文化和教育,可能被战争打断,但它们的生命力更长久。
卫礼贤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典籍的德译,他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他翻译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家语》《礼记》《易经》《吕氏春秋》《道德经》《列子》《庄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经籍。这些译本迅速使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入了德国思想界主流之中,影响到黑塞、荣格这样的大作家和思想家。
1930年3月1日卫礼贤在德国图宾根去世,终年57岁。他的身影化为永恒,与青岛紧密联系在一起。
笔与枪,哪一个有力量?书与剑,哪一个不朽?文化的力量可以穿透百年的历史烟云,仍然散发魅力。卫礼贤活在青岛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文脉之中。
卫礼贤原名为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年5月10日出生于斯图加特。在他57年的生命历程中,有20多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以一名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青岛,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1899年,卫礼贤乘船来中国时,他无法预料到将在青岛逐渐完成身份的转变从传教士到汉学家。他更无法预料到自己会拥有一颗“中国心灵”,他的灵魂深深地被中国文化所吸引,学说中国话,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像一块海绵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吸取文化的滋养,成为20世纪享誉全球的汉学家。
卫礼贤在青岛,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崛起,更重要的是,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成了青岛里程碑式的人物。
1900年,卫礼贤在青岛创办了礼贤书院(今青岛九中),这是青岛的第一所新式中学,开风气之先。1904年,卫礼贤建议中德政府联合创办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德华大学,1909年建成)。他组织尊孔文社,弘扬儒家文化,和当时在青岛的文化名流聚会。在他的《中国心灵》一书中有“青岛的故人们”一节,卫礼贤生动地描绘了他与在青岛的劳乃宣、康有为、辜鸿铭、恭亲王溥伟等人的交往。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卫礼贤与清朝的遗老遗少的交往,显示出一幅清末民初的政治画卷。1914年,卫礼贤创建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青岛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亦为中国早期图书馆之一。然而好景不长,日本与德国的战争在青岛这个美丽的城市点燃硝烟,卫礼贤和他在青岛的故人们星散世界各地。
1914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无暇东顾,对德国参战,进攻青岛。卫礼贤的日记记录下日德战争的全过程 。卫礼贤一战期间在青岛的日记,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冷静客观,他虽然是一个德国人,但没有局限在“爱国主义的热情”来记录战事。卫礼贤的伟大就在于此,他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看待眼前发生的战事,以及德国的战败。他的目光看得更加深远 ,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中西文化交流 ,致力于青岛的教育事业。文化和教育,可能被战争打断,但它们的生命力更长久。
卫礼贤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典籍的德译,他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他翻译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家语》《礼记》《易经》《吕氏春秋》《道德经》《列子》《庄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经籍。这些译本迅速使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入了德国思想界主流之中,影响到黑塞、荣格这样的大作家和思想家。
1930年3月1日卫礼贤在德国图宾根去世,终年57岁。他的身影化为永恒,与青岛紧密联系在一起。
笔与枪,哪一个有力量?书与剑,哪一个不朽?文化的力量可以穿透百年的历史烟云,仍然散发魅力。卫礼贤活在青岛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文脉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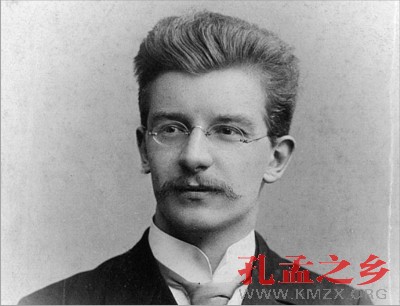
生于1873年的卫礼贤,曾在青岛生活20余年。他不仅在此兴建了礼贤书院,还结交了大批中国文化名流,并参与到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中来。晚年的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中国心灵》,我们翻阅了本书,并走访了一些研究卫礼贤的学者及其日记的中文翻译,试图找寻出这位“德国孔夫子”的青岛足迹和他对中国的看法。
初到青岛之印象
“我离开这个黄浦江边混乱又繁忙的城市继续北上。一日,烟雾笼罩的崂山忽然升起在海面之上,不一会儿小火轮到达了青岛。旅客们下船登上舢板,这是一种平底、划桨的小船。小船随波起伏摇摆,到岸方息。”
《中国心灵·从上海到青岛》
1899年5月,已经通过神学考试4年的卫礼贤受到基督教同善会的差遣,到青岛来传教。
“在意大利的欢歌笑语中,我做好了前往美丽东方的准备。”然而,初到中国的他却有些失望,“上海的喧嚣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但这不是真正的中国。”卫礼贤认为这个城市是英国人刻板作风和海港居民的嘈杂互相妥协的产物,他尤其不喜欢这里别扭的中式英语。随后他坐船北上到达了青岛,当晚住在了大鲍岛区。当时的那里“欧式房屋一间也没有,连旅馆也尚未完工,人们都住在中国渔民简陋的茅屋里……街道正在修建,山上开着又宽又深的沙沟。”而卫礼贤住进了一家破旧的“安琪儿旅馆”,一早起来,他发现一只公鸡正在他的床头打鸣。于此同时,“青岛的村庄正在流行伤寒和痢疾”。
尽管如此,卫礼贤对青岛还是充满好奇。他近乎疯狂地学习汉语,“连睡觉都在学”。并在一个中国仆人的陪伴下,决定骑马去即墨镇游玩。
一路上,青岛乡村风景让他十分兴奋,“田野长满了玉米和高粱,雨后的高粱竟然比我骑在马上还高。我还看到了大豆、花生,又香又甜的山东鸭梨,红光闪闪的柿子,这玩意和西红柿还不一样”,而当地的民风也让他印象深刻。“晚上,姑娘媳妇们坐在门洞里说笑,老年人在他们的保护神关帝庙里,或者大树下,抽着旱烟袋,讨论村中事务或天下大事,对此他们常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在即墨,他这个外国人的出现引发一阵骚动,不过“当地的清朝官员身体不佳,我很幸运地躲过了拜见。”他看到自由玩耍的孩子时,突然感叹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小孩像中国小孩一样允许其自由发展……不受束缚长大的孩子最终会成为有用并高尚的人。”
然而,卫礼贤此行最重大的发现却是“中国的集市上,经常有成群的苦力在干活,他们被认为懒惰、粗鲁、狡猾……但我发现,他们也是人,有人的欢笑与痛苦,不得不为生活奋斗,不得不通过自己聪明和忍耐来讨生活,不得不以或直或曲的方式走自己的路。”通过这些走访见闻,卫礼贤很快融入到了青岛人的日常生活中,并开始反思西方的传教方式和自己来中国的目的。晚年的他回忆说:“我在中国没有为一个人施过洗,所以我也许能够走得更近,真正触摸到中国人的本质”。
调解胶济铁路高密风波
“中国人心中有这样一种迷信,认为修铁路会惊动黄土下的列祖列宗。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地势较低的地区,人们担心修铁路而筑起的堤坝会增加洪水的危险……总之,修铁路遭到抵制。于是,全副武装的德国兵被派到了青岛和高密之间。”
《中国心灵·调停筑路矛盾》
从卫礼贤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曾经游览过很多地方,潍县、青州、济南、泰山、曲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曲阜,他参加了孔子后裔的婚礼;在济南,他得到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的接待。后来他还到山西看过云岗石窟,到杭州看过西湖和园林,并到过北京、南京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地武昌。但他在青岛遇到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德国人因修建胶济铁路而引发的农民抗争。
1899年,卫礼贤来中国时,正是义和团风起云涌之时,卫礼贤称其为“秘密社团的秘密运动”,并认为正是由于“国内到处都有外国人,他们用武力和不平等的手段四处渗透”才引发这场农民起义运动。但他对义和团的做法仍然表示了反对,“运动笼罩着浓厚的迷信色彩,并且发展为公开的狂热……到处都有集会,到处都有被鼓动起来的人们。”这种情况下,卫礼贤和所有在青岛的德国人都感到了不安,尽管“山东巡抚袁世凯不相信那些义和团团民刀枪不入的胡言乱语”,但驻扎德国的军官还是“武装到了牙齿”,随时防范可能的起义。相比之下“我家恐怕是当时唯一没有准备武器的人家了。”
而与此同时,德国人为连通青岛和济南而修筑胶济铁路在高密境内遇到了麻烦。1899年11月,高密境内爆发了大规模农民抗德阻路的武装斗争,使得工程被迫停工近一年,这件事也成为后来莫言小说《檀香刑》的创作来源。针对这件事的起因,卫礼贤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他认为除了“迷信”外,更多的是由于双方存在着“误解”。在听说德国军队血腥地镇压了一个起义的村庄后,他冒着危险主动提出去做中德双方的调解者。他先是说服了德国军队推迟行动 ,又去动员懒惰的清朝官员,最后深入到村庄劝诫村民交出武器以示诚意。最终 ,事件达成了和解,德国人适当调整了工程方案,并增加对村民的补偿,而村民也不再破坏铁路的工程进度。卫礼贤则收到了村民制作的“很多丝绸刺绣装饰品”,以及“中国政府给我的一枚纽扣状的东西”。这可能指的是日后1906年清政府赏给卫礼贤的四品官印。卫礼贤画像 周辉 绘卫礼贤家人合影 (周辉提供)礼贤书院成立初期,卫礼贤与部分的教职工合影。
创办礼贤书院
“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过一种与基督教精神相符的简单生活,通过在学校和医院的工作来影响别人,和他们一起生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今天的中国人对世界的其他部分已经有所了解,取得理解的过程中可能还会发生一些令人惊奇的过程,但”义和团”这样的事是再也不会发生的。”
《中国心灵·对传教方式的反思》
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卫礼贤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是怀着其他的目的加入教会的,他们想通过教会的特殊地位来支持自己。比如利用教会报复和自己有矛盾的邻居。”而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后,卫礼贤决定改变自己的传教方式。
1900年,卫礼贤在青岛创办了礼贤书院(今青岛九中),明确规定“凡入校习德文的少年,必须精通中文”,很多学生报名踊跃,规模不断扩大。校址最初设在自己家中,1901年在大鲍岛东山建了正式校舍,卫礼贤从德国与瑞士合办的同善教会筹措到了经费,但他既不建教堂也不传教而是用于办学。他自任监督(校长),聘请了一批通现代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等的教师,也有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师。1902年底,山东巡抚周馥到胶澳访问,周馥参观礼贤书院后,授予该校学生参加山东大学堂考试的资格。
初到青岛之印象
“我离开这个黄浦江边混乱又繁忙的城市继续北上。一日,烟雾笼罩的崂山忽然升起在海面之上,不一会儿小火轮到达了青岛。旅客们下船登上舢板,这是一种平底、划桨的小船。小船随波起伏摇摆,到岸方息。”
《中国心灵·从上海到青岛》
1899年5月,已经通过神学考试4年的卫礼贤受到基督教同善会的差遣,到青岛来传教。
“在意大利的欢歌笑语中,我做好了前往美丽东方的准备。”然而,初到中国的他却有些失望,“上海的喧嚣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但这不是真正的中国。”卫礼贤认为这个城市是英国人刻板作风和海港居民的嘈杂互相妥协的产物,他尤其不喜欢这里别扭的中式英语。随后他坐船北上到达了青岛,当晚住在了大鲍岛区。当时的那里“欧式房屋一间也没有,连旅馆也尚未完工,人们都住在中国渔民简陋的茅屋里……街道正在修建,山上开着又宽又深的沙沟。”而卫礼贤住进了一家破旧的“安琪儿旅馆”,一早起来,他发现一只公鸡正在他的床头打鸣。于此同时,“青岛的村庄正在流行伤寒和痢疾”。
尽管如此,卫礼贤对青岛还是充满好奇。他近乎疯狂地学习汉语,“连睡觉都在学”。并在一个中国仆人的陪伴下,决定骑马去即墨镇游玩。
一路上,青岛乡村风景让他十分兴奋,“田野长满了玉米和高粱,雨后的高粱竟然比我骑在马上还高。我还看到了大豆、花生,又香又甜的山东鸭梨,红光闪闪的柿子,这玩意和西红柿还不一样”,而当地的民风也让他印象深刻。“晚上,姑娘媳妇们坐在门洞里说笑,老年人在他们的保护神关帝庙里,或者大树下,抽着旱烟袋,讨论村中事务或天下大事,对此他们常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在即墨,他这个外国人的出现引发一阵骚动,不过“当地的清朝官员身体不佳,我很幸运地躲过了拜见。”他看到自由玩耍的孩子时,突然感叹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小孩像中国小孩一样允许其自由发展……不受束缚长大的孩子最终会成为有用并高尚的人。”
然而,卫礼贤此行最重大的发现却是“中国的集市上,经常有成群的苦力在干活,他们被认为懒惰、粗鲁、狡猾……但我发现,他们也是人,有人的欢笑与痛苦,不得不为生活奋斗,不得不通过自己聪明和忍耐来讨生活,不得不以或直或曲的方式走自己的路。”通过这些走访见闻,卫礼贤很快融入到了青岛人的日常生活中,并开始反思西方的传教方式和自己来中国的目的。晚年的他回忆说:“我在中国没有为一个人施过洗,所以我也许能够走得更近,真正触摸到中国人的本质”。
调解胶济铁路高密风波
“中国人心中有这样一种迷信,认为修铁路会惊动黄土下的列祖列宗。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地势较低的地区,人们担心修铁路而筑起的堤坝会增加洪水的危险……总之,修铁路遭到抵制。于是,全副武装的德国兵被派到了青岛和高密之间。”
《中国心灵·调停筑路矛盾》
从卫礼贤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曾经游览过很多地方,潍县、青州、济南、泰山、曲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曲阜,他参加了孔子后裔的婚礼;在济南,他得到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的接待。后来他还到山西看过云岗石窟,到杭州看过西湖和园林,并到过北京、南京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地武昌。但他在青岛遇到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德国人因修建胶济铁路而引发的农民抗争。
1899年,卫礼贤来中国时,正是义和团风起云涌之时,卫礼贤称其为“秘密社团的秘密运动”,并认为正是由于“国内到处都有外国人,他们用武力和不平等的手段四处渗透”才引发这场农民起义运动。但他对义和团的做法仍然表示了反对,“运动笼罩着浓厚的迷信色彩,并且发展为公开的狂热……到处都有集会,到处都有被鼓动起来的人们。”这种情况下,卫礼贤和所有在青岛的德国人都感到了不安,尽管“山东巡抚袁世凯不相信那些义和团团民刀枪不入的胡言乱语”,但驻扎德国的军官还是“武装到了牙齿”,随时防范可能的起义。相比之下“我家恐怕是当时唯一没有准备武器的人家了。”
而与此同时,德国人为连通青岛和济南而修筑胶济铁路在高密境内遇到了麻烦。1899年11月,高密境内爆发了大规模农民抗德阻路的武装斗争,使得工程被迫停工近一年,这件事也成为后来莫言小说《檀香刑》的创作来源。针对这件事的起因,卫礼贤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他认为除了“迷信”外,更多的是由于双方存在着“误解”。在听说德国军队血腥地镇压了一个起义的村庄后,他冒着危险主动提出去做中德双方的调解者。他先是说服了德国军队推迟行动 ,又去动员懒惰的清朝官员,最后深入到村庄劝诫村民交出武器以示诚意。最终 ,事件达成了和解,德国人适当调整了工程方案,并增加对村民的补偿,而村民也不再破坏铁路的工程进度。卫礼贤则收到了村民制作的“很多丝绸刺绣装饰品”,以及“中国政府给我的一枚纽扣状的东西”。这可能指的是日后1906年清政府赏给卫礼贤的四品官印。卫礼贤画像 周辉 绘卫礼贤家人合影 (周辉提供)礼贤书院成立初期,卫礼贤与部分的教职工合影。
创办礼贤书院
“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过一种与基督教精神相符的简单生活,通过在学校和医院的工作来影响别人,和他们一起生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今天的中国人对世界的其他部分已经有所了解,取得理解的过程中可能还会发生一些令人惊奇的过程,但”义和团”这样的事是再也不会发生的。”
《中国心灵·对传教方式的反思》
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卫礼贤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是怀着其他的目的加入教会的,他们想通过教会的特殊地位来支持自己。比如利用教会报复和自己有矛盾的邻居。”而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后,卫礼贤决定改变自己的传教方式。
1900年,卫礼贤在青岛创办了礼贤书院(今青岛九中),明确规定“凡入校习德文的少年,必须精通中文”,很多学生报名踊跃,规模不断扩大。校址最初设在自己家中,1901年在大鲍岛东山建了正式校舍,卫礼贤从德国与瑞士合办的同善教会筹措到了经费,但他既不建教堂也不传教而是用于办学。他自任监督(校长),聘请了一批通现代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等的教师,也有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师。1902年底,山东巡抚周馥到胶澳访问,周馥参观礼贤书院后,授予该校学生参加山东大学堂考试的资格。
曾在青岛九中学习过的文史学者鲁海介绍:礼贤书院开办初期,卫礼贤夫妇亲任德文教师,聘贡生傅兰升教汉文,文会馆毕业生朱宝琛教数学。1903年新校舍建成,有教学楼、实验室,从德国运来了中学理化试验器材、地图、动植物标本。另有宿舍和餐厅,宿舍也是两人一间。1906年,礼贤书院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举行了盛大毕业典礼,胶澳总督学务委员会主任参加典礼。此外,卫礼贤还组织尊孔文社,弘扬儒家文化,并在此和当时在青岛的文化名流聚会 。1914年,卫礼贤创建尊孔文社藏书楼 。这是青岛第一个现代图书馆,亦为中国早期图书馆之一。他还以妻子的名字开办过一所“美懿女中”。
后来礼贤书院改名礼贤中学,是青岛历史最悠久的中学。解放后,礼贤中学改为青岛九中。早期礼贤书院的校舍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拆除重建 。卫礼贤曾向德国当局建议在青岛办一所大学,德国与清政府采纳了这一意见,在青岛开办了青岛特别高等学校(亦称德华大学)。1914年该校迁往上海,与同济医学专科学校合并为同济大学。1913年,基督教同善会女子学校的学生在教会山(大鲍岛东山)上过复活节。
追忆青岛的故人们
“恭亲王正好也在这里,他现在每天都在写日记,记下发生的一切。他带着困惑问我,是不是天上根本没有彗星,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么大的战争,天上一定会降下慧星显示先兆的。于是,我努力给他解释了关于彗星的现代理论。”
1914年10月8日《卫礼贤日记》
在卫礼贤的《中国心灵》中,专门有一章讲述了他在青岛结识的朋友,命名为《青岛的故人们》,当年卫礼贤在尊孔文社每周举办讲座由中德两国学者轮流主讲,德方主要为德华大学教师,中方为一些逊清遗老,这其中有恭亲王溥伟、两江总督周馥,学部副大臣刘廷琛,法部侍郎王垿,财政大臣周学熙,以及“活力四射的辜鸿铭”、“持保皇观点的康有为”等人,其中他和劳乃宣的交往最深。
劳乃宣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我国著名音韵学家,辛亥革命后避居青岛。卫礼贤和他的结识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中国心灵》中记载“我梦中有一个眼神友好,胡子雪白的老人来探访我,他自称”崂山”,要我去探寻古老山岳的秘密,他一消失我立刻就醒了。”在做完这个奇怪的梦不久,卫礼贤在曾任山东巡抚周馥的引荐下认识了劳乃宣,而且“他和我梦中遇见的那个老人像极了”。此后,思想保守的劳乃宣与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卫礼贤十分相投,他和卫礼贤一起运营礼贤书院、创办尊孔文社藏书楼 ,后来他还协助卫礼贤翻译了《易经》等中国经典,而卫礼贤也一直尊称他为“劳大师 ”。张勋复辟期间,卫礼贤还通过劳乃宣给溥仪皇帝传话,建议溥仪娶一位德国公主以获得德国对复辟的支持。
另一位和卫礼贤有着较深交往的则是恭亲王溥伟,他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奕訢的嫡孙,避居青岛的他和卫礼贤交往甚多。“他是一个自傲清高、天真率直的人,喜欢命令别人,显得难以接近,但他清正廉洁。他曾把家中的财宝全部卖掉,希望有朝一日恢复过去的朝廷……他始终拖着他那条精心梳理的大辫子以显示身份。”但经过多年的奔波,这位亲王渐渐变得平易近人起来,“有一次,他主动找我,想让我用小提琴表演一段欧洲音乐,他听得如痴如醉,他说这和中国最优秀的音乐是相通的。”再后来的日子里,卫礼贤经常和这位亲王一起讨论中国的政治、北京的故宫以及“他当年如何用颤抖的双手给老太后(慈禧)递交上一份报告。”德国驻扎青岛的“美洲豹”炮舰,日德青岛之战后期被德军自行炸沉。德占青岛时期最早完成的街道之一海因里希亲王大街(今广西路)俾斯麦山(青岛山)上的德军阵地。
记录战火中的青岛
“日本人的一架飞机飞过来,并投下炸弹,其中一枚炸死了台东镇的一个中国男子。这个人之前为了能有一个庇护的场所,特意向我们的红十字会缴纳了会费。但他还是需要在田间劳作。可能他潜意识以为自己已经加入了红十字会,所以才会这么不小心。在中国,红十字会一直是一个饱受曲解的组织。”
1914年10月23日《卫礼贤日记》
1914年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德国的殖民地,青岛的德军遭到了日本的进攻。在把自己家人送到安全的地带之后,卫礼贤选择了坚守青岛,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 ,会址就设在礼贤书院。而与他一起留下来的还有“不愿去共和领土”的恭亲王。
“卫礼贤的一战中的日记是他所有日记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内容讲述了1914年8月到11月间,他被困青岛期间的见闻。”作为该日记的中文翻译,秦俊峰认为这本日记中充满对战争的厌恶和对中国人的同情。从日记中我们看出,尽管这是日德之间的战争(战争初期,北洋政府表示中立)。但“中国民众陷入恐慌,人们像潮水一般拥向了开动的火车。”而在青岛的普通德国人也被组成“一支市民军,据说日后会提拔成正规的国防军,因此满大街都是怪诞的士兵。”与此同时,卫礼贤则继续进展自己的慈善事业,在他的努力下连日本领事也加入了红十字会。
战争是残酷的,“日军的炮火十分激烈,青岛城也有可能被完全摧毁。”“晚上,坐落在四方的军营被击中后燃起大火,照亮了整个夜空。而今天恰好是团圆的中秋节。”“日本人大炮几乎击中了胶州街道上所有的交叉路口,看上去是从海上发起的进攻。”“一枚炸弹掉进了屋子,没有爆炸,他摸了一下这个铁家伙,说:”这东西倒是烫得很”……这场青岛之战持续了3个月,而就在战争刚开始不久,面对差距明显的实力对比,卫礼贤便已经做出了德国将战败的预测,并感叹“现在一切都要过去了,青岛也成了历史。如果再给我们十年的时间,青岛会一直延伸到沧口,现在才刚刚开始,中国人便已经蜂拥而来了。毫无疑问,这里本可以发展成上海和天津那样,可是如今这一切都要成为历史了。”
战后的青岛被日军占领,卫礼贤因为没有直接参加战斗而被免于追究,他继续留在青岛照顾这里的200余名德国人和一些中国难民。1924年,在辞去北大名誉教授后他回到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以介绍、研究中国文化,联络德中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为目的。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中国学刊》(后更名为《汉学》)。在此期间,他还邀请胡适到德国作学术报告,陪诗人徐志摩作了欧洲之旅。
#p#副标题#e#
后来礼贤书院改名礼贤中学,是青岛历史最悠久的中学。解放后,礼贤中学改为青岛九中。早期礼贤书院的校舍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拆除重建 。卫礼贤曾向德国当局建议在青岛办一所大学,德国与清政府采纳了这一意见,在青岛开办了青岛特别高等学校(亦称德华大学)。1914年该校迁往上海,与同济医学专科学校合并为同济大学。1913年,基督教同善会女子学校的学生在教会山(大鲍岛东山)上过复活节。
追忆青岛的故人们
“恭亲王正好也在这里,他现在每天都在写日记,记下发生的一切。他带着困惑问我,是不是天上根本没有彗星,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么大的战争,天上一定会降下慧星显示先兆的。于是,我努力给他解释了关于彗星的现代理论。”
1914年10月8日《卫礼贤日记》
在卫礼贤的《中国心灵》中,专门有一章讲述了他在青岛结识的朋友,命名为《青岛的故人们》,当年卫礼贤在尊孔文社每周举办讲座由中德两国学者轮流主讲,德方主要为德华大学教师,中方为一些逊清遗老,这其中有恭亲王溥伟、两江总督周馥,学部副大臣刘廷琛,法部侍郎王垿,财政大臣周学熙,以及“活力四射的辜鸿铭”、“持保皇观点的康有为”等人,其中他和劳乃宣的交往最深。
劳乃宣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我国著名音韵学家,辛亥革命后避居青岛。卫礼贤和他的结识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中国心灵》中记载“我梦中有一个眼神友好,胡子雪白的老人来探访我,他自称”崂山”,要我去探寻古老山岳的秘密,他一消失我立刻就醒了。”在做完这个奇怪的梦不久,卫礼贤在曾任山东巡抚周馥的引荐下认识了劳乃宣,而且“他和我梦中遇见的那个老人像极了”。此后,思想保守的劳乃宣与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卫礼贤十分相投,他和卫礼贤一起运营礼贤书院、创办尊孔文社藏书楼 ,后来他还协助卫礼贤翻译了《易经》等中国经典,而卫礼贤也一直尊称他为“劳大师 ”。张勋复辟期间,卫礼贤还通过劳乃宣给溥仪皇帝传话,建议溥仪娶一位德国公主以获得德国对复辟的支持。
另一位和卫礼贤有着较深交往的则是恭亲王溥伟,他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奕訢的嫡孙,避居青岛的他和卫礼贤交往甚多。“他是一个自傲清高、天真率直的人,喜欢命令别人,显得难以接近,但他清正廉洁。他曾把家中的财宝全部卖掉,希望有朝一日恢复过去的朝廷……他始终拖着他那条精心梳理的大辫子以显示身份。”但经过多年的奔波,这位亲王渐渐变得平易近人起来,“有一次,他主动找我,想让我用小提琴表演一段欧洲音乐,他听得如痴如醉,他说这和中国最优秀的音乐是相通的。”再后来的日子里,卫礼贤经常和这位亲王一起讨论中国的政治、北京的故宫以及“他当年如何用颤抖的双手给老太后(慈禧)递交上一份报告。”德国驻扎青岛的“美洲豹”炮舰,日德青岛之战后期被德军自行炸沉。德占青岛时期最早完成的街道之一海因里希亲王大街(今广西路)俾斯麦山(青岛山)上的德军阵地。
记录战火中的青岛
“日本人的一架飞机飞过来,并投下炸弹,其中一枚炸死了台东镇的一个中国男子。这个人之前为了能有一个庇护的场所,特意向我们的红十字会缴纳了会费。但他还是需要在田间劳作。可能他潜意识以为自己已经加入了红十字会,所以才会这么不小心。在中国,红十字会一直是一个饱受曲解的组织。”
1914年10月23日《卫礼贤日记》
1914年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德国的殖民地,青岛的德军遭到了日本的进攻。在把自己家人送到安全的地带之后,卫礼贤选择了坚守青岛,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 ,会址就设在礼贤书院。而与他一起留下来的还有“不愿去共和领土”的恭亲王。
“卫礼贤的一战中的日记是他所有日记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内容讲述了1914年8月到11月间,他被困青岛期间的见闻。”作为该日记的中文翻译,秦俊峰认为这本日记中充满对战争的厌恶和对中国人的同情。从日记中我们看出,尽管这是日德之间的战争(战争初期,北洋政府表示中立)。但“中国民众陷入恐慌,人们像潮水一般拥向了开动的火车。”而在青岛的普通德国人也被组成“一支市民军,据说日后会提拔成正规的国防军,因此满大街都是怪诞的士兵。”与此同时,卫礼贤则继续进展自己的慈善事业,在他的努力下连日本领事也加入了红十字会。
战争是残酷的,“日军的炮火十分激烈,青岛城也有可能被完全摧毁。”“晚上,坐落在四方的军营被击中后燃起大火,照亮了整个夜空。而今天恰好是团圆的中秋节。”“日本人大炮几乎击中了胶州街道上所有的交叉路口,看上去是从海上发起的进攻。”“一枚炸弹掉进了屋子,没有爆炸,他摸了一下这个铁家伙,说:”这东西倒是烫得很”……这场青岛之战持续了3个月,而就在战争刚开始不久,面对差距明显的实力对比,卫礼贤便已经做出了德国将战败的预测,并感叹“现在一切都要过去了,青岛也成了历史。如果再给我们十年的时间,青岛会一直延伸到沧口,现在才刚刚开始,中国人便已经蜂拥而来了。毫无疑问,这里本可以发展成上海和天津那样,可是如今这一切都要成为历史了。”
战后的青岛被日军占领,卫礼贤因为没有直接参加战斗而被免于追究,他继续留在青岛照顾这里的200余名德国人和一些中国难民。1924年,在辞去北大名誉教授后他回到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以介绍、研究中国文化,联络德中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为目的。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中国学刊》(后更名为《汉学》)。在此期间,他还邀请胡适到德国作学术报告,陪诗人徐志摩作了欧洲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