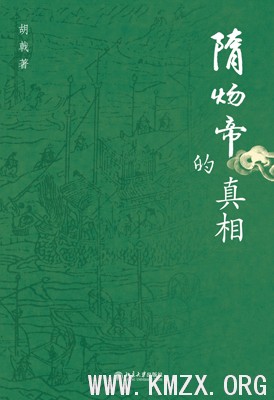
摘自:《隋炀帝的真相》 胡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开皇十年(590),晋王杨广第二次出镇扬州,到开皇二十年(600)为皇太子时去职,在扬州任上整整十年。这次镇扬州,他被赋予很大权力。但他是两度带兵南下的征服者,要被南方人民接受,必须改善自己的形象。汲取苏威用惩罚的办法强制推行五教和政令,激起南方普遍反抗的教训,杨广改而求诸宗教和儒学。这一时期里,他十分引人注目地对佛教和儒学表现出极大的热心,目的是利用宗教和儒学沟通南北僧俗隔阂已久的心声,消弭南方人民的反隋感情。在平陈、平叛后继续镇守扬州的晋王,将这视为自己头等的政治使命。这是他和南方佛教首领智等一批和尚,及以柳为首的一批文人学士亲密交往的大背景。首先说佛教。隋文帝杨坚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的般若寺中,由一位女尼抚养大。独孤皇后更是笃信佛教。家庭佞佛的传统,从小就影响了杨广的信仰,他接受佛教不奇怪,但在平叛之后的开皇十一年(591),杨广亲受菩萨戒,甘心做一名菩萨弟子,事情就有点出格了。晋王杨广这次受戒,仪式空前隆重。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扬州大听寺设千僧斋,专门从天台山请来智做他的戒师。智禅师(538—597)创立了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宗派之一——天台宗,当时已是南方著名的宗教领袖。杨广特别想借重这位高僧的名望,扩大自己的影响。佛籍中现在还留存着晋王和智往来的几十封书信。智为这位表示愿“生生世世长为大师弟子”的亲王说了许多好话,竭诚拥戴杨广为“总持菩萨”,还给杨广送去“菩萨天冠”,为他的统治添上一道宗教的灵光。智当然也有自己的目的,他与这位王爷交往,可以不时得到许多布施。更要紧的是,不久前北朝周武帝灭佛的余悸,和平陈以来战乱的破坏,使僧侣们急于要在最高统治层中找保护伞。智曾一再致书杨广,径请他做匡山(庐山)东林、峰顶两寺和天台、玉泉、十住三寺的檀越,即施主。杨广和智相互照应,彼此谅解。智圆寂后,杨广遣使吊唁,并设周忌,真诚地哀悼。开皇十八年(598),即为智常驻的天台山修天台寺。大业元年(605),改名国清寺,取意“寺若立,国土即清”。迄今,隋炀帝创建的这座名寺,仍与山东灵岩寺、湖北玉泉寺、江苏栖霞寺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刹,因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被日本佛教天台宗奉为祖庭。至今一株隋梅生意盎然,主干神奇地枯而复生,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再说儒学。隋炀帝雅好儒士,读书撰述,整理图书,一反隋文帝的做法,大力办学,在文化建设上多有建树。他在扬州总管任上时,大量网罗才学之士,现在知名的王府学士和扬州博士便有柳、诸葛颍、虞世南、王胄、王、朱、庾自直、潘徽、虞绰等人,其中柳来自梁国,诸葛颍来自北齐,其余虞世南等都来自陈国,全是声誉颇高的文人。杨广闻名礼聘来的,还有一个薛道衡(539—609),平陈时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兼掌文翰。杨广求才心切,让人转告他,从扬州路走,届时上奏留他在王府。可是薛道衡不愿意,用汉王谅之计,出江陵道而去。杨广对此心里很不痛快。
当时隋文帝“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强制转变文风的复古运动,对杨广也有影响。
当时印刷术在难产中,自秦代以来,图书数遭厄难,北周图书,方盈万卷,平齐所得,才加五千。隋文帝按牛弘建议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于是“经籍渐备”,整理成三万余卷。比较隋初的一万五千余卷御书单本,和隋文帝后来整理好、藏于宫中及秘书监的那三万余卷,隋炀帝这又组织撰写的一万七千余卷新书,是分量很大的成果。他在位时又命担任了秘书监的柳整理西京嘉则殿藏书。实在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隋炀帝著有文集五十五卷,卷帙浩繁,为隋代之冠。《全隋文》中存四卷,《全隋诗》中存诗四五十首。那些夹带脂粉轻薄气味的梁陈宫体诗,叫人无法恭维,但另一些气势磅礴的政论和不乏高古清俊诗意的佳作,总是要让人对这位有很高文化素养的皇帝刮目相看。
恃宠夺嫡入主东宫自隋朝建立到开皇末年的二十年间,晋王杨广由一个快乐的少年皇子,成长为一位颇有阅历的青年王爷,在他到了风度翩翩的而立之年时,已有灿烂可观的文治武功可以夸耀。这时他不再安分于宗法制度给他安排的将来称臣于长兄的卑屈地位,进而觊觎皇权。向来认为,母后独孤氏在帮助次子杨广实现夺取其长子杨勇太子位的计划中,起了关键作用。关于这场夺宗之谋,我们且就先从他俩的这位著名母亲讲起。隋文帝独孤皇后,传称河南洛阳人,是后来改的籍贯。独孤氏本是匈奴族屠各之裔。其父独孤信(503—557)是云中(今山西大同)人,曾祖独孤俟尼“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因家焉”。独孤信和宇文泰在武川为乡里,“少相友善”。后来都卷入六镇与河北起兵事件,辗转赴长安,同为西魏府兵的八柱国大将军。独孤信官至大司马,是关陇集团中一个典型的军事贵族之家。后因与赵贵同谋诛执政宇文护,事败自尽。但他的长女为周明敬皇后,第四女为唐元贞皇后(追尊为元皇帝的李渊父亲李的妻子),第七女即隋文帝独孤皇后,史称:“周、隋及皇家(唐)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史家所谓后性妒忌,“高祖甚宠惮之”,本质上是对其家族的敬畏。独孤家族的支持,对隋室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独孤皇后干政很深,皇帝上朝她也形影相随。“上每临朝,后辄与上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即匡谏,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寝,相顾欣然。”独孤皇后对隋文帝的私生活也管束极严。杨广争宠,乖巧地在母亲身上下工夫。他“美姿仪,性敏慧”⑥,从小为父母钟爱。长大后,“敬接朝臣,礼极卑屈,声名籍甚,冠于诸王”。⑦太子勇也“颇好学,解属辞赋,性宽仁和厚”,但是“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大大咧咧,被处处投父母所好的兄弟钻了空子。对比之下,他俩给父母留下好恶迥然不同的印象。独孤后最恨姬妾生孕,杨勇却多内宠,最受爱宠的云昭训和后宫其他姬妾,为他生了十个儿子,气得独孤后直骂猪儿狗崽,“有如许豚犬”,而自己亲自选定的太子妃元氏,却被拒于夫妻生活之外,开皇十一年(591)忽然暴亡,被怀疑是毒死的,“后弥不平”。杨广却“唯共萧妃居处”,他学父母“后庭有子皆不育”。杨广一生仅三个儿子,独孤后生前见到的长子昭、次子,都是萧妃所生,“后由是数称广贤”。⑤隋文帝夫妻比较节俭,“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⑥这里是说,他们平时的衣着也不讲究,因为豪华的涂料印染或手绘的礼服是不能洗涤的。独孤后拒收价值八百万一箧的明珠,因不事涂抹化妆,宫中竟找不出一两胡粉,这些在当时都传为美谈。杨勇却“文饰蜀铠”,隋文帝很不高兴地训诫他:“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⑦而“晋王来朝,车马侍从,皆为俭素”,人们早就传说,杨广“躬履节俭,有主上之风”。⑧
杨坚夫妇偶尔出访,在次子杨广家里看到的,是老丑的佣人,素缣屏帐,乐器的弦也是断的,还满是尘埃,皇帝以为杨广不好声色,对他赞不绝口,“由是爱之特异诸子”。有一年冬至日,杨勇穿上太子法服,在东宫设乐,受百官朝贺,引起隋文帝猜疑,下诏禁止此类僭越行动,“自此恩宠始衰”。杨广在入朝后将还镇扬州时入宫告辞,向母后泣诉:“不知何罪,失爱东宫,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谗谮生于投抒,鸩毒遇于杯勺,是用勤忧积念,惧履危亡。”激发母亲无限伤感,“自是后决意欲废勇立广矣”。受《隋书》的观点“废太子立晋王广,皆后之谋也”的影响,历来认为促使隋文帝废立太子的都是上面这些故事,杨勇奢侈失宠,杨广矫情夺嫡成功,独孤皇后是决定性的人物。实际上,这是隋文帝本人的重大抉择,由于对长子杨勇失去了信任和耐心,他转而选择了在各方面都有出色表现的次子杨广为自己的储君。因为,正如《剑桥中国史》的作者指出的,杨广“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像他父亲最早预期的那样,他最适合承当巩固和加强隋朝的伟大事业”。隋文帝对杨勇本无恶感,自己建隋称帝之初,毫不犹豫地立了世子杨勇为皇太子。“上使太子勇参决军国政事,时有损益;上皆纳之”。⑤当时准备按检逃户和徙民实边两事,就是采纳杨勇的意见而放弃的。后来他“文饰蜀铠”和令东宫妇人“服兵帜”⑥等一些事,也还说不上多么奢侈荒唐。他的失宠,主要是隋文帝疑心太子不肖,有篡权行迹,“畏其加害,如防大敌”。⑦为此把强健者全部调离,削弱了东宫宿卫。实际似是过虑,证据并不足。杨坚临终前又想恢复杨勇的太子位,就说明当年废他并无实据,要不然议废时李纲也不敢冒死为杨勇辩护。更主要的原因是,当太子杨勇越来越让皇帝失望的时候,晋王杨广却如一颗明星在政坛上冉冉升起,随到之处,建功立业,饮誉朝野。隋文帝是一位有心于国事的“近代之良主”⑧,他自己开创的新国家,已经宏图初展的开皇之治,要成为万代基业,必须把权力移交给一位最有能力的儿子。于是他抛弃了嫡长子继承的陋规,毅然决定行太子废立的大事。依杨广当时的表现来说,隋文帝做这样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隋书》说他:“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并非确论。决定是他本人理智地做出的,当然也是在独孤后推动下做出的,其间杨素一党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再说事变的具体进程,其中体现了杨素一党——上引《隋书》中所说“邪臣”——的作用。最早在扬州为杨广策划夺宗计的是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刺史宇文述和扬州总管司马张衡。宇文述也是来自武川的军事贵族,平陈时任行军总管,在杨广身边率三万军从六合渡江作战。他认为,废立问题上“能移主上者,唯杨素耳”,而杨素遇事,只找他弟弟内史令杨约商量。宇文述表示愿赴京师见杨约共图废立。宇文述带着杨广的大量金宝入关,用赌博佯输的办法把金宝都给了杨约,然后向杨约说明这是晋王所赐和晋王的用意,于是联络好了杨约。杨素一向与太子不和,为长保荣禄,与晋王一拍即合。独孤后也给杨素送钱,让他活动废立太子之事。杨广还通过段达收买东宫幸臣姬威,让他给杨素提供太子行动的情报。太子知道自己处境岌岌可危,占候也是“皇太子废退之象”,便“于后园之内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时于中寝息,布衣草褥,冀以当之”。但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了。开皇二十年(600)九月廷议时,杨素发难,姬威作证,隋文帝表态:“此儿不堪承嗣久矣。……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也……今欲废之,以安天下。”左卫大将军元试图劝阻,被下狱。杨勇及其诸子和党羽都被禁锢,“杨素舞文巧诋,锻炼以成其狱”。自一年前杨勇的儿女亲家高被罢官,孤立无援的太子,败局便已注定了。十月的一天,隋文帝戎服陈兵,御武德殿,宣诏废杨勇及其子、女为王、公主者。杨勇最初心惊胆战,知不杀他,泣下流襟,舞蹈而去。在场的许多官员沉默地看着,为他难过。十一月,杨广被立为皇太子。废太子仍囚于东宫,交给新太子管束。杨勇回过味来,感到自己委屈,一心申冤上诉,被杨广阻遏,只好爬到树上大叫,希望隔墙的宫中听到,报告皇帝接见他。可是杨素挡驾,说杨勇“情志昏乱”,已精神失常。皇帝信了这话,不再理会。杨勇因而终生未得再与父皇见面的机会,杨广的夺宗之谋获得了彻底的成功。隋文帝也毫不怀疑,这是自己意志的胜利。正像唐太宗也是以次子秦王的身份夺宗,取代长兄太子建成,进而掌握皇权一样,他们原来是否有正统的身份,钻营太子位采取什么手段等等,都不是我们臧否历史人物的着眼点。坦白地说,如果他们确实比做了太子的兄长更有治国才能,那么他们不甘在窝窝囊囊的皇兄治下无所作为地虚度人生,奋起夺过权力来做一番事业的话,尽管是对不起哥哥,却未必是历史的不幸。既然没有民主制度安排他们走别的路,那么阴谋和政变作为专制政治的伴生物,就是一种历史的出路。我们又何必拘泥于迂腐的正统观念,不看历史运动的实质内容,而仅就夺权的形式做肤浅的批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