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是一支唢呐,惊涛拍岸,却终成一管洞箫,呜咽低回。
这管洞箫,就在大运河畔的小城济宁鸣奏着,几十年如一日,不分寒暑,不计昼夜,并使这座运河古城成为中国农具史学科的研究重镇。当《中国工程技术史大系》丛书中的分册《中国农业机械史》的撰写重任,受中科院的邀请、无可争议地落在济宁市周昕的肩上的时候;当北京、南京等大都市的博士生,受导师的引荐,千里迢迢,前来济宁专门向一个名叫周昕的人就撰写中国农具史博士论文问题求教的时候——这座曾经吸引过李白、杜甫的古城,便显出了自己的尊贵与澹定。
只是,这些从大都市赶来的学子,是不大容易找到周昕的。他住在一所缩在城郊深巷之中的老年公寓里,还好骑着一辆三轮车出去看病或查寻资料。他们就是在大街上与周昕迎头相遇,也绝对不会相信蹬着如此的三轮车的人,会是他们崇敬的周先生。三轮车当然破旧得很了,一个轮子还缠着绷带,生锈的车把上,挂着一个饱满却已老化成暗灰色的塑料袋,袋中装着圆珠笔、小本、眼镜、身份证、老年证和急救药等——岁月与疾病已经摧残得他步履维艰了。再难找,学子们也一定要找到他,因为这位中国农具发展史学科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是不能越过的。
2005年,当几乎凝聚了周昕毕生精力的142万字的《中国农具发展史》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之后,他便最终奠定了自己中国农具史学科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的地位。这个定位,不是我说的,是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教授等一批重量级农史专家们给出的公正评价,并说周昕是这个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从这部书出版至今,他又用了整整5年的生命,撰写出了50万字的《中国农具发展史补遗》,令中国农业科技界再次为之惊叹。
他原来有着更大的梦想。那是在五十四前的1956年,作为山东工学院学生的周昕在学院图书馆看到了英国人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捧书在手,热血蒸腾,一个宏大的计划便在胸中萌生: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写?炎黄子孙不是可以写出更好的中国科技史吗?而我为什么就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只是当初生的牛犊屡被鞭、轭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庞大的计划是无法完成的。于是,他便将这个宏大的目标,缩减为中国农具史范畴,并从此不再动摇。即使如此,又谈何容易?但是就是在生命极限的考验面前,他也没有退缩过,并为此几乎耗去了退休前的全部业余时间和退休后的全部时光。这种没有退缩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他内心深处的清醒的认识:中国是一个具有上万年农业文化的文明古国,而与农业相辅相伴走过了上万年光辉历程、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农具,却没有一部能够展现其发展全貌的信史,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大遗憾,也是一种耻辱。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周昕,就是这样一位来自底层、为国分忧的“脊梁”吧?
曾经长时间地混乱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之中,甚至在“文革”中因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被隔离审查两年多之久,但是他让梦想在煎熬里强硬地活着。在那样的年代,一个寂寞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农具史这个寂寞的领域里默默地求索不已。还有嫉妒与私利牵动下的争斗与撕咬,当然更多的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复杂而又维妙的人际关系等等,都会以常态的形式,试图扰乱他执着的脚步。当岁月的潮汐过后,再来看他留下的一直向前的清晰足迹,我终于发现,他固然会受到名目繁多的干扰,但他绝不被裹挟,甚至最终保持住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不为所动的宁静与凝视。
他知道,稍一动摇,也许刚刚开启的中国农具史的大门,又会严严地关上。一旦关上,重启的日子则会遥遥无期了,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农具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考验正未有穷期。
先是几种重大疾病的袭来。冠心病来了,脑梗塞来了,末稍神经炎来了。心慌,眩晕,疼痛,对于他连挪动几步都已成为一种奢侈。当然还有不可抗拒的衰老的到来,都在向他发出着讪笑。而真正理解他、帮助他并时里刻里照顾他生活起居的老伴的去世,则是对他的又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这个看似柔弱、已是风烛残年的老者,有着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渔夫老人圣地亚哥的力量与坚忍不拔,“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圣地亚哥语)。疾病与打击,只能是一次次地催促他与生命抢时间。他悲怆而又昂然地向前走去,他说我不怕死,可我死不起,本已寂寥的中国农具史学科,不能没有我这个知己。他是那样地爱它,越发地不忍让它从沉寂到泯灭,他要让它重生为再不消失的一面中华文明史的明镜。想到,说到,更已做到,在《中国农具发展史》之前,周昕已陆续撰写出版了 《农具史话》、《〈耒耜经〉和陆龟蒙》、《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淡水养鱼机械及应用》、《药茶》等专著及几十篇论文。而他编绘、制作、装裱并收入近千幅古农具图谱的百米长卷《中国古农具图鉴》,已经被中国农业博物馆作为珍品收藏,并由此被聘为中国农业博物馆馆员。
为了向前跋涉,他硬是在古稀之年学会了电脑打字与应用技术,并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当肉体的病老侵袭得几失尊严的时候,他让自己富博而又灵感迭出的大脑和已然热血沸腾的精神,加速地运转着。就在他一点一点的积累并建筑起中国农具发展史的大厦的时候,他也完成了自己生命的锻造与重生——打破桎梏获得自由与解放、实现价值获得欢乐与尊严。
75岁又多病缠身的周昕,还在为中国农具史学科的深化与拓展独自从事着艰巨的劳动。一个炎热的傍晚,我去黄庄公寓看他,这位从济宁市农机研究所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正在做着《中国农具发展史补遗》的完善与修订。一旁的饭盒里,正盛着还没有顾上吃的晚饭:已经泡得有些膀的面条和因为放的时间长而有些发黑的炖茄子。一杆长长的竹箫,静静地斜靠在满是书的床头上。他无奈地告诉我,这管陪了他几十年的箫,如今已经没有气力吹响了。不过,最让他心焦的,还是《中国农具发展史补遗》的不能出版。对于中国农具发展史的研究,不仅耗费了他毕生的精力,也耗去了他大部分的工资与积蓄。现在,病着,医药费又贵,出版也就更加困难了。
在上面提到的鲁迅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里,还有着这样的话:“这一类的人们(指埋头苦干的中国的脊梁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鲁迅说的那个旧的时代早已过去。周昕当然是处在一个新的好的时代,他与他的研究成果,不会被抹杀,该是会被我们所记得。
采访完也构思好了,刚想把周昕的事情写出来,手就受了点伤。但我还是坚持用受了伤的手把这篇文章在电脑上打写出来,因为我有个比照,周昕的身心受过那样多的创痛,不是仍然坚持写出了他的获得华东地区及山东省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的《中国农具发展史》吗?不是他还在孜孜不倦地为抢救、保护、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继续编撰着《中国农具文化图谱》而在与生命赛跑吗?于是,他让我想起那不知疲倦的钟摆,总是日夜兼程地行走着,走着……
李木生 2010-7-12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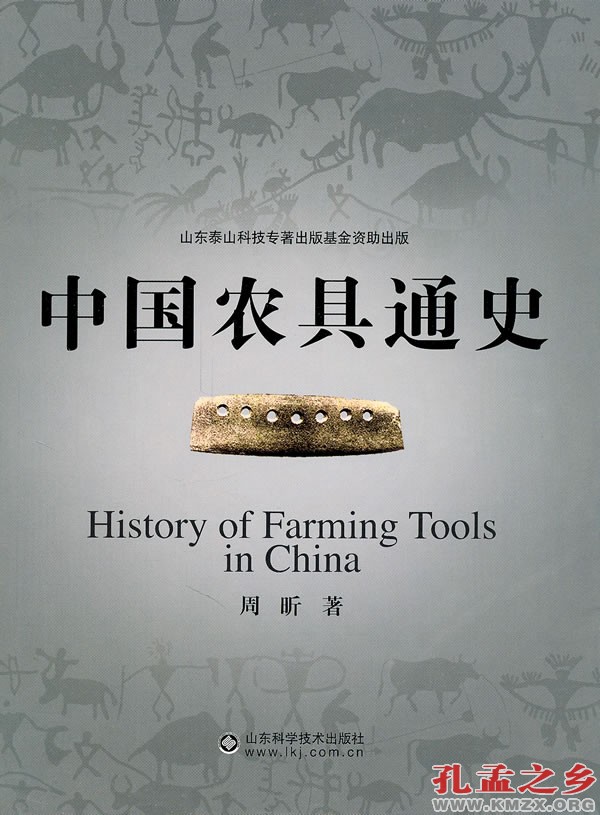
《中国农具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