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1957年生于上海,现居上海,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2012年9月,朱大可推出《神话》一书,承载了其厘清中国文化起源、重塑中国文化精神的追求。此前,他著有《燃烧的迷津》、《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等作品,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诸多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直指当下文化之精神病灶。
近日,记者邮件专访朱大可,请他解读文化批评在中国当下的现实图景,评点教育移民、互联网暴力等文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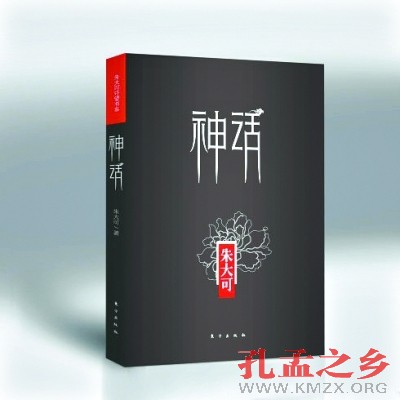
朱大可谈《神话》
文化批评仍是一个年幼的领域
复杂语境里做文化批评,首先要尽可能拓展观点的边界,同时又必须学会踩线而不越线的技巧。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文化批评,它是戴着镣铐的思想舞蹈。
读+:文化批评者的立场应该在何处?“批评”的含义与意义到底是什么?
朱大可:文化批评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文化批评具有某种否定性,而广义的文化批评,就是针对文化对象(文本)展开独立阐释。文化批评者应当学会这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但它们总是被人混淆。21世纪初,我们引入了这个概念,并且在同济大学建立了文化批评研究所,当时“文化批评”无人了解,而十多年过去之后,这个词已经成为流行语词,而“文化批评家”则如雨后春笋。这是出乎意料的结果。
读+:你对文化现象全方位的关注及“一剑封喉”式的批评,令人想到鲁迅的话“一个都不放过”。你如何评价身为文化批评者的自己?
朱大可:媒体的赞誉过分了。哪能“一剑封喉”?顶多就是挠个痒痒而已。跟鲁迅他老人家相比,更是望尘莫及。文化批评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它需要专业技术和技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批评家就是文化行业的鉴定师,其工作范围是对各种文化事件和“产品”做出准确的研判。既然是一种专业活儿,就一定会出错。我也是个常出错的人。我知道自己的限定性。
读+:1986年你发表《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引起的后续反应留下的是黑色记忆。今天文化批评的环境与那时相比如何?做文化批评时需不需要考虑尺度或自我设限?
朱大可:就文化的大环境而言,1985~1986两年,是1949年后最开放的时期,但电影圈的局部环境,则比较险恶。今天的文化格局正好相反,整体环境远不如当初,但一些局部领域,却有一些宽松的意味。在这样的复杂语境里做文化批评,首先要尽可能拓展观点的边界,同时又必须学会踩线而不越线的技巧。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文化批评,它是戴着镣铐的思想舞蹈。
读+:在文化批评的道路上,你是否觉得孤单或后继无人?
朱大可:文化批评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显学”,吸纳了大批中青年人才,其中许多人是从文学评论圈转行过来的。这是一种令人鼓舞的迹象。但很多转行者并未掌握文化批评的基本工具和技术,如文化哲学、符号学、语言学、诗学、阐释学等等,这令许多“文化批评”文字看起来不够“专业”。它不是跟文学评论相似,就是跟时评相混。文化批评至今仍是一个年幼的领域。
读+:你发出的诸多警示有没有收到一点效果?
朱大可:我不知道。今天的言说,必然要面对强大的“广场效应”。你置身于一个十多亿人的互联网广场,所有人都在抢着发言,而你的声音还没有被传播,就已消失在大面积的喧嚣之中。在这样的混乱格局中,你能够指望以蚊子般的微小体量,喊出“时代的最强音”么?
我们还滞留在推销“孔子”的原始阶段
现在人们不仅缅怀1947年的民国宪法、民国人物、民国风情、民国趣味,而且也会怀念共和国早期的工业产品,所有这些对旧日时光的追忆,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含蓄否决。
读+:为什么说2012年中国正处于罕见的历史拐点?
朱大可:2012年之所以被视为转折点,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坛在这一年换届,更是由于它同时是玛雅历和中国历的大转换时刻。任何一种有智慧的顶层设计,若不利用它来推动大幅度政治改革,就将坐失历史良机。
读+:“民国+早期共和国”的双料怀旧在2012年大行其道,原因是什么?
朱大可:它主要源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现在人们不仅缅怀1947年的民国宪法、民国人物、民国风情、民国趣味,而且也会怀念共和国早期的工业产品,所有这些对旧日时光的追忆,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含蓄否决。当然,这里也有对民族工业产品质量的未来期待。
读+:请你点评一下2012年的关键词之一“你幸福吗”。
朱大可:在当下的时局里,问别人“你幸福吗”之类的问题,要么很愚蠢,要么是在指桑骂槐。所以央视的新闻采访,必然会遭到网民的嘲笑。“幸福感”是最不可靠的感受,在大饥荒年代,任何一只干瘪的红薯,都能换来巨大的幸福感。“文革”时期,“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的“幸福感”,据说是民众最普遍的政治感受。但那玩意儿能当作衡量“盛世”的真实标准吗?
读+:当下国人的物质消费欲望高涨,但国家话语仍然自我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错位应该怎么厘清?
朱大可:这的确是一种非常古怪的错位,但官方表述显然很不准确。欲望被大面积点燃了,但另一方面,物质生产的数量在猛烈增长,但质量很差,大多数日常消费品仍处于低级模仿阶段,工艺粗陋,品质低下,无法满足日益精细化的欲望谱系。文化消费品更是如此,我们至今还滞留在向世界推销“孔子”的原始阶段。
读+: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是否同等?有什么是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
朱大可:很抱歉,暂时还看不到这样的文本,但我相信它们正在某处静悄悄地生长。
“流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范畴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居民社会和流氓社会的复合体,这是一个坚硬的历史传统。不解决“流氓化”问题,中国就很难兑现“文化复兴”的梦想。
读+:你为何放弃了文学事业?今天是看好还是看衰中国文学?
朱大可:我的神话研究,可以算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但对中国当代文学,却不敢有什么太多的奢望。21世纪以来,文学面对着世界和本土的双重衰退,我看不到有什么拯救它的力量。除非我们在谈论的是一种广义的文学,它囊括了电影、电视和新媒体之类的叙事媒介。
读+:当今中国文坛,有没有让你觉得欣慰的作家、读物、媒体形式或文学现象。他/它的价值在哪里?
朱大可:这个比较复杂,很难一言蔽之。我首先看好民间诗歌运动,只有诗歌才能拯救被互联网弄坏的汉语。我也看好北村、阎连科这样的长篇小说作家,他们的中国叙事,有望为下一代人提供历史真相。我也看好新媒体如微电影、Ipad多维电子杂志、手机阅读之类,这是一个巨大的传播平台,能为文化复苏提供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
读+: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相继在电影界失去了所向披靡的地位,原因在哪里?
朱大可:第五代导演走向衰退,这首先是个无法逃避的生理性现象。拍电影是一种很苦的力气活儿,需要足够的体魄和精神能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崛起的作家、导演、作曲家、理论家,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似乎都站在时间的临界点上。大概只有极少数人能超越这个大限。当年我曾经欢送第三、四代导演的“离场”,并目击了第五代导演的诞生,历史好像到了重演的时刻。我们正在加入被欢送的人群。
读+:如果我们能迎来一场新文化运动,会是从哪个方面开始的?你期望它达到什么目的?你正在撰写的《中国上古神系》一书,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朱大可: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于白话文,也就是日常语言工具。本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的启动,可能有多重方向。就我个人而言,重塑中国文化精神,必须厘清中国文化起源,而文化起源的追溯,则必须从上古神话开始。这就是我多年来研究中国上古神系的原因。
读+:《神话》一书中,“流氓话语”及你对禹、李白、唐寅、徐渭等“流氓”群像的塑造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如此关心“流氓”?它在今天有什么映射?
朱大可:“流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范畴,不深入讨论“流氓”,就无法对中国历史做出准确的评判。当下的中国社会(如果它有“社会”的话),是“居民社会”和“流氓社会”的复合体,这是一个坚硬的历史传统。“毛”时代用铁腕整合了分裂的两者,“邓”时代又分裂回去了。“流氓”不仅是一种身份特征,而且是一种日常哲学,我称之为“流氓精神”,它是支撑国人存在的价值核心。不解决“流氓化”问题,中国就很难兑现“文化复兴”的梦想。
互联网正在考验我们的耐性
一些网民还没有学会如何以理性和有教养的方式发表不同意见,没有掌握正确的公共平台交往方式,更没有掌握从多重互相矛盾的资讯中获取真相的能力。
读+:你对教育体制的批评很多,觉得需要触及的要害在哪儿?
朱大可:中国教育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弄错了教育目标:它要培养的究竟是顺从的小乖,还是独立、完整、健康的人格?其次是弄错了培养手段:它要用“应试教育”来培养听命于“标准答案”的傻瓜,还是要通过质疑、挑战和批判性思维来塑造创造性人才?
读+:身为体制中人,父母除了教育移民,还能做些什么?
朱大可:家庭教育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矫正,但这种自我矫正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家长自身的头脑。如果家长本身具有良好的独立思考素质,就能帮助孩子躲避伤害。
读+:你现在给本科生上课,说要把中学教育造成的错误“洗”回来?
朱大可:重要的不是告诉学生什么是对与错,问题的关键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也就是以人类普世价值为标准,对不同来源、互相打架的资讯,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只要具备了这种能力,学生就能正确地观察和分析事物,而无须依赖老师给出的任何答案。
读+:微博在迅速兴起,很快也被许多人放弃。这一现象背后是什么?微博上缺乏理性和头脑的言论如此之多,愤怒、谩骂的东西又能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说明了什么?
朱大可:中国特色的微博,是一个功能复杂的容器,它既是批评时弊和推动进步的公共对话平台,也是公共厕所和心理治疗室,所以,大量出现“脑残”言论是正常的。许多人退出微博而转向微信,就是对这种“微博污染”的严重不适。一些网民还没有学会如何以理性和有教养的方式发表不同意见,没有掌握正确的公共平台交往方式,更没有掌握从多重互相矛盾的资讯中获取真相的能力。而培养这种独立反思能力以及“互联网礼仪”,至少还要10年以上的时间。互联网正在考验我们的耐性。
#p#副标题#e#
一个都不放过
(记者翟晓林)上世纪80年代,身为第三代导演的谢晋在电影界占据着至高地位,29岁的“后生”朱大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非议,认为它向观众提供的“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道德神经”,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其陈旧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
放在骂战普遍的当下,这一批评大约只能掀起一小阵浪花。但在当时,却引发激烈的争鸣与批判浪潮,在高层的干预下,许多与朱大可沾上点关系的人甚至受株连丢掉了铁饭碗。
尽管结果悲情,但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朱大可的《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一文,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这是文化批评者朱大可发出的第一声强音。
此后,朱大可转向文学领域,相继出版《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等,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2001年,朱大可在澳大利亚待了7年后回国,再度开始“一剑封喉”式的文化批评,他对卫慧“文学叫春”及余秋雨“文化口红”的概括,获得了比批评对象自身更强劲的生命力。
近30年过去,当年欢送“第三代”的朱大可自言也“加入被欢送的人群”,但时时更新的专栏与博客见证着他对当下文化现象仍在实时关注。他对权力至上文化格局带来的众多丑陋具象建筑的批评,对微博“既是公共对话平台,也是公共厕所和心理治疗室”的概括,对莫言“在‘诺贝尔圣徒’与‘乡愿作家’之间挣扎”的评价,与时俱进,宝刀未老。
朱大可的文化批评并不止于狭义的否定式批评。但在进行这种批评时,他广涉文化哲学、中国文化、上古神话及当代大众文化,“一个都不放过”。就连评价自己,他也表示:“我常犯错误,知道自己的罩门所在,而且30至40岁之后,便在经历一个缓慢的衰退和下降过程。”
批评之外,朱大可也在构建。他对上古神系的梳理,对“流氓史”、“流氓精神”的探讨,也正是在其所述“思想、文学和影像全面衰退的语境中”,进行“恐龙式”书写、维系汉语文化底线的尝试。
朱大可
武汉开通地铁,这相当于为人们开辟了一块新的生活空间。这里的生活,自然包括文化生活。
今天我们的译见版,做了条纽约地铁里的阅读。从中,我获得了一个新的信息,原来纽约地铁关闭了网络和手机信号。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很多人拿起了纸质书本,开始了地铁阅读,从而与涂鸦等等一道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
从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文化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忧心忡忡,认为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人和时间越来越多,而坚持阅读纸质书籍的人和时间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将拉低现代人的思维和文化水准,也将拉低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的创造力。
这种忧虑是有必要的,但可能未必确切。在古代,无论中外,文盲的人口占比都很高,识文断字的是少数人,能够在思想和文化上有所创造的则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是,许多古代文明依然做出了伟大的思想文化创造,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津津乐道于那些古典社会的文化黄金时代。
这个道理,对于今天的阅读信息与阅读书籍的关系来说,也是一样的。现代社会从社会和政治层面打破了古代的金字塔结构,而追求一种扁平的社会,但在文化的世界,金字塔可能是个永恒的结构。
从这里,我也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政治的问题。我很好奇,纽约是经过了什么样的程序而关闭了地铁的网络和手机信号,这里面是否遭遇过激烈的民意反弹?同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国的城市,会怎么样?
地铁首先是一个大运量的交通运载工具,地铁的空间也可以成为文化的空间,这使得地铁是在运人而不是运货。文化的空间有它自然生成的一面,需要时间。
假以时日,我们相信武汉的地铁空间也能够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空间,能够与其他东西一道,为这座正在快速变化和再造的城市,催生新的都市文化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