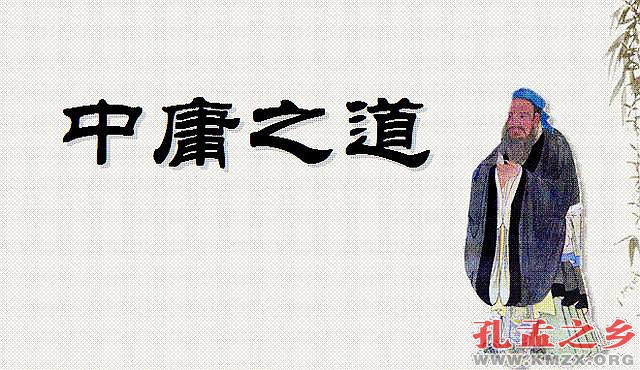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中庸”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论语•雍也》记载说:“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将“中庸”思想视为“至德”,是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精准把握和对自身思想体系的深刻升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庸”曾经饱受非议。时至当下,很多人依然存有误解,认为“中庸”之道只不过是“折中主义”、“调和路线”、“好好先生”、“和稀泥”的代名词。然而,事实却绝非如此。“中”是不断变化的,“中”乃“时中”,它代表了儒学思想的最高境界。
“中庸”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孔子和儒家关于中庸思想的精华汇集在《中庸》一书中。《中庸》为孔子裔孙子思所作,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朱熹作《中庸集注》,《中庸》就成了儒家四书之一,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庸曾经饱受非议,甚至时至当下,在很多人看来,中庸之道只不过是“折中主义”、“调和路线”、“好好先生”、“和稀泥”的代名词。比如,总有些人认为,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就在于中国人“太中庸”了,以为中国人因为太讲中庸而丧失了锐气。于是,身受中庸之道影响的人们开始自我反思、自我批判。中庸之道在国人的眼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反而是中国近代数百年来裹足不前、闭关自守的罪魁祸首。中庸之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
然而,实际上中庸绝对不等于所谓的“折中主义”。孔子就非常反对无原则的折中与调和,他认为那些“和稀泥”的人就是“乡愿”,而“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是孔子所坚决反对的。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庸呢?中庸之道看上去非常高深,其实它的意涵相对简明。《说文》云:“庸,用也。”古代典籍中,“庸”作“用”讲的例子很多,如《尧典》:“畴咨若时登庸”;《诗•王风•兔爰》:“我生之初,尚无庸”;《诗•齐风•南山》:“齐子庸止”。实际上,“庸”的本义就是“用”。从《易经》来看,“庸”在先秦时期与“用”字相通,“庸”即是“用”,而非“庸人”、“庸碌”之“庸”。“中庸”应该叫“中用”,即“用中”,也就是如何使用“中道”。理解中庸的关键是,中庸这个词实际上是个偏正结构,而不是个并列结构。即“中”与“庸”两字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中”,简单说来“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中道”。这样理解,就可以避免许多对“中庸”的偏见。郑玄《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中”就是做事情要把握分寸,将事情处理得恰到好处。如何在实践中用“中”?如何把握中道?看似容易,实际上却需要相当的知识与思想境界。“中”是不断变化的,就好像我们平常用的秤,物体重量的增减会不断地打破平衡,为了维持平衡,就需要相应地不断地移动秤砣。只要合理地理解和运用中庸,就可以发现它的神奇之处。
一、三代明王与“中庸”之道
孔子曾经盛赞舜之“持中”:“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论语•尧曰》篇有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中”可以说是自古相传的明王之道的核心内容,新近出土的清华简《保训》篇很能够说明这一点。《保训》篇是周文王给武王的遗言,而文武之间授受的核心即是“中”,文王说:“发,朕疾适甚,恐不及女训。”可见“中”的重要性。接着文王又讲述了舜和殷之先祖上甲微“求中”和“假中”的故事。文王最后说道:
呜呼!发,敬哉!朕闻兹不久,久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轻!日不足,惟宿不祥。
周文王对武王提出的要求是严格的,而且他希望武王要认真遵行,不可松懈。为了周朝的安宁与发展,要对“中”保持一个诚敬的态度。从文献记载来看,文王以后,周人对文王谆谆告诫的“中”是认真执行了的。
《逸周书》记载,武王临终时,对辅佐成王的周公同样是谆谆嘱托,要他“克中”。《五权解》载:
维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呜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维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维敬哉!先后小子,勤在维政之失……克中无苗,以保小子于位……维中是以,以长小子于位,实维永宁。
克,允之。苗,借为谬。所谓“克中无苗”,就是做到适中无邪;以,用也。所谓“维中是以”,就是“维中是用”。因此我们不难看到武王对“中”的重视。
舜将“中”传于禹,文王又将之传于武王,武王又传于周公,可见“中”的价值及其重要性。而且我们看到,“中”与古之明王之道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否做到“中”,是能否得到天命的关键之所在。“中”可以说是儒家道统的核心概念,宋儒所推崇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实际上就是对“中”的精妙阐释。清华简《保训》篇的问世,印证了从尧、舜到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孟的道统传承,宋儒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二、西周时期的“中道”思想
西周时期,“中道”思想很受重视。西周是礼乐文化发展的高峰期,而礼乐文化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实质毋宁说是“中”。礼可以说是“中”的标准,符合礼的就是“中”,否则就不是“中”。所以《逸周书•武训解》曰:“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又说:“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很明显礼的实质就是“尚中”,或者说做到“尚中”才符合礼。西周职官中有“师氏”,其具体职掌就是邦国之士是否合乎法度、礼仪。《周礼•地官司徒》载:“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郑玄注曰“教之者,使识旧事也。中,中礼者也;失,失礼者也。”
除了礼仪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是周代的刑罚之“中”。刑罚之“中”就是在执行刑律或者狱讼判决时的最佳效果。因为刑罚不应是为了处罚而处罚,而是为了惩戒他人,以达到“无讼”的最佳状态。实际上,刑罚就是为了追求最佳的教育效果。
周代发展出了“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但是礼乐并非是治理国家的唯一途径。周人提倡“德主刑辅”,礼乐之外的刑罚同样是治理国家所必不可少的,只是处于次要的地位。礼乐与刑法看似南辕北辙,实际上,它们内在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刑罚同样强调“中”,《周礼•秋官司寇》云:
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郑玄曰:“‘中’谓罪正所定。”另外,同书多次出现“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之语。郑玄注云:“受中,谓受狱讼之成也。郑司农云:士师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狱也。中者,刑罚之中也。故《论语》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此处所谓的“中”就是指的“狱讼之成”、“罪正坐定”,也即经过审判所定之刑罚,将这种判罚的结果称之为“中”。从中可见周代刑罚所追求的是什么。《周礼》同篇又载:“以此三法者(三刺、三宥、三赦之法),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可见周代之刑罚并不是为了刑罚而刑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周代“以刑教中”的思想。据《周礼》,大司徒的职责是所谓“十二教”,“以刑教中”就是其中之一:
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刑罚的根本在于教化,只有刑罚得“中”,即对于一定的犯罪行为给予相应的刑罚,使得犯罪者和百姓都心悦诚服,使民知所畏惧,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复归于礼法,而不为暴乱之事了。
三、孔子与“中庸”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对于自古明王心传之“中道”思想大为推崇。他对于前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孔子这里,中庸之道被发挥到了极致。
孔子对于“中”的重视,突出表现在以下这句话中: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论语•子路》)
为什么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因为礼乐与刑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中”,礼乐不兴,则无礼乐之中,无礼乐之中,则无刑罚之中。如果刑罚做不到“中”,则是很危险的事情。在政治实践中,力求做到刑罚之“中”十分重要,这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关系到人心之向背。刑罚是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如果连刑罚都失去了正义性,那么百姓就真的无所措手足了,因为他们失去了价值判断的标准,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做了。这样的话,社会就会无可避免地陷于混乱之中。孔子强调有德之君的言传身教,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不论是礼乐还是刑罚,其目的都是为了求“中”,所谓的“中”就是为民所立的一个标尺,让他们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绝对不能做,并在他们心中树立起一种价值观的基点,使他们有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礼乐与刑罚实际上都是教化的方式,而关键却在于“中”。
在孔子这里,“中”的思想被发挥到了极致。“中”是孔子思想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畴,是孔子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孔子之为人变幻莫测,通达无极。孟子曾经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万章下》),是“圣”之集大成者。所谓的“圣之时”,按照《中庸》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时中”。孔子曾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什么是“时中”?“时中”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根据事情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处事方式。孔子可以说将“时中”这一概念践行到了极致。他曾自谓自己与古之圣贤的“言中伦,行中虑”、“身中清,废中权”的处事方式不同,孔子采取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实际上,这就是“时中”。但是孔子之“无可无不可”并不是毫无原则的隐忍或者“放浪形骸”,而是有一个重要基点的,这就是“义”,这个“义”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做任何事情可以没有固定的方式方法,可以随着事态的变化而不断转变处事方式,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天马行空的恣意妄为,而是必须在“义”可以容纳的范围之内。只要合于义,就可以达于天道,那就没什么不可为的了。《史记•孔子世家》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件事:
(孔子)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於匡,今又遇难於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离陈去卫,经过蒲地,正逢卫国公叔氏据蒲叛卫,他们将孔子一行人团团围住。孔子有个弟子名叫公良孺,此时正好随从护卫孔子。公良孺甚有勇力,与蒲人战斗,誓死保卫孔子的安全,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最后蒲人敌公良孺不过,因此决定和孔子妥协:只要孔子不去卫国,现在就可以立即放孔子等人离去。孔子答应了蒲人的要求,两方盟誓。但是孔子还是违反盟约去了卫国,就连子贡也不解地问道:“可以不按盟约行事吗?”孔子回答:“我们是因为受到要挟才进行盟誓,这是不公平的,不受神灵的佑护。”孔子的回答高屋建瓴,变幻莫测,自谓天命之所居,神人之所佑,待人行事,上达天道,非常人可及。这可以说孔子“时中”思想的最佳注脚。
虽然孔子“从周”,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位复古主义者。他说过:“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中庸》)孔子的“时中”智慧就在于因时行止,在于“进退无恒”,在于“知至至之”、“知终终之”,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而且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孳乳而生的,绝非后世庸碌钝塞之辈所能了然的。
#p#副标题#e#孟子继承了孔子“时中”的思想,针对时人“举一而废百”的弊端,孟子着重强调了“权”。他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认为“中”、“权”结合才能正确践行“中庸”。实际上孟子的“权”本来就是孔子“时中”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是后人愚钝不察,未能理解孔子“中庸”思想的妙处罢了。
中庸之道看似极高明,实则极简便易行;看似简便易行,实却又使人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感。世之于中庸明且行之者,少之又少;乱而毁之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故中庸只有神奇,既是高明的神奇也是简易的神奇。中庸有何尴尬?云中庸之尴尬者,实为反中庸之小人也,正如夫子所言“无忌惮”之“小人”也,因其无忌惮,故诋毁圣人之言,诳惑天下众生。
【参考文献】:
1.杨朝明:《“清华简”〈保训〉与“文武之政”》,《管子学刊》,2012年第2期。
2.杨朝明:《周文王遗训与儒家“中庸”思想》,贾磊磊、杨朝明主编:《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
3.杨朝明:《孔子的“中道”哲学及其意义》,载:Wang jing、Gerd kaminski、Richard Trappi .Konfuzius ——Mensch,M, Machtund Mythos. Wien(维也纳),2013年。
(原载《正本清源说孔子》 作者: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