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为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
鲁迅与济宁嘉祥武氏祠汉代石刻画像结缘,最早发生于他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自1913年9月11日“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癸丑书帐:胡君孟乐赠武梁祠画像佚存石拓本十枚)之后,鲁迅对武氏祠汉画像拓片的搜集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据鲁迅日记和历年书帐不完全统计:1915年4月19日,午后同陈师曾之小市,买《金石萃编》一束;同年4月21日,至直隶官书局买《金石续编》一部十二本;同年4月28日,从图书馆假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景写家所藏本;同年5月1日,午后往琉璃厂买杂汉画像四枚,武梁祠画像并题记拓本等五十一枚(乙卯书帐:武氏祠堂画像并题记拓本五十一枚);同年5月6日,上午得西泠印社所寄《两汉金石记》六册;同年5月8日,下午往直隶官书局买《金石萃编》一部五十册;同年5月16日,午后至留黎厂买武氏祠新出土画像一枚;同年5月23日,下午往留黎厂买济宁州画像一枚;同年6月8日,夜修订《金石萃编》讫;同年9月12日,得上海蟫隐庐所寄来《金石萃编校字记》一册;同年10月4日,上午富华阁送来杂汉画像拓本一百三十七枚(乙卯书帐:嘉祥零散汉画像拓本一百三十七枚);同年10月30日,下午往留黎厂买《孔子见老子画像》一枚,旧拓,孔像略损。纸坊集画像、不知名画像各一枚(乙卯书帐:济宁杂画像二枚)。1916年正月12日,汪玉堂代买山东金石保存所藏石拓本全分来,计百十七枚(丙辰书帐细目:汉画像十纸跋一纸。嘉祥画像十纸跋一纸);同年3月25日,下午往留黎厂买济宁州学所藏汉魏石刻拓本一分,大小共十七枚(丙辰书帐细目:执金吾丞武荣碑一枚,孔子见老子画像一枚);同年4月13日书帐:济宁李家楼画像一枚;同年5月20日,午后往留黎厂买《武班碑》并阴二枚;同年5月28日,下午往留黎厂买旧拓《武荣碑》一枚。1917年正月9日,午后往留黎厂直隶官书局取《金石苑》一部六册,去年预约;同年5月6日,上午往留黎厂买《隶释》《隶续》附汪本《隶释刊误》共八册;同年5月31日,杨莘士寄拓本一束,凡汉画像十枚……皆济南金石保存所藏石。1934年至1936年,鲁迅托人棰拓、寄赠、购买嘉祥及南阳等汉画像拓片二百二十余枚、《金石萃编补略》等相关资料六十余本。
自1912年5月到京后,鲁迅便隔三岔五或单独或同行一二人向琉璃厂去“淘宝”,他在《壬子北行以后书帐》中这样写道:“审自五月至年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真实地记录了鲁迅在京期间从未间断过的收藏生活,同时也是他一生,包括武氏祠汉画像拓片在内收藏活动的一个缩影。

济宁嘉祥南武山武氏祠汉画像石拓片
鲁迅不仅倾心于对武氏祠汉画像拓片的收集,而且更善于及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与友人的交流、杂文创作、讲演以及推动中国的新兴版画事业中来。1923年1月8日,他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汉石刻中之人首蛇身像,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像外,亦殊不多……今附上三枚”。1924年10月,他在《坟·说胡须》中写道:“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男子的胡须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引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1927年鲁迅在广州,他在《朝花夕拾》后记中写道:“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和雕刻古来的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但手头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1935年,他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讲到:“然而倘是画像,却也间或遇见的。我曾经见过三次……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在武氏祠和嘉祥汉画像石中,孔子见老子是画像内容的重要题材,乾隆五十一年黄易曾将在武氏祠中发现的孔子见老子一石移至济宁州学与武荣碑一起保存。联系上文,鲁迅见过的孔子见老子像当出自武氏祠和嘉祥汉画像石。鲁迅就是这样对武氏祠汉画像的内容俯拾即来,随时运用到杂文创作中。
鲁迅对武氏祠汉画像的评价。据许寿裳说:鲁迅在1917年曾告诉他:“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是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1935年9月9日,鲁迅致李桦信:“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1935年2月4日,鲁迅在致李桦的另一封信中说:“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精神……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1934年2月11日,鲁迅致姚克信中说:“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生活状态,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此像《金石萃编》及《金石索》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同年2月20日,鲁迅致姚克的另一封信中说:“武梁祠画像新拓本,已颇模糊,北平大约每套十元上下可得。又有孝堂山画像,亦汉刻,似十幅,内有战斗,刑戮,卤簿……等图,价或只四五元,亦颇可供参考”。同年3月24日,鲁迅致姚克:“汉唐画像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模糊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先生见过玻璃版印之李毅士教授之《长恨歌画意》没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与‘梅郎’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画数千年前之中国人,就已有了辫子,而且身穿马蹄袖袍子乎。绍介古代人物画之事,可见也不可缓”。同年6月21日,鲁迅致郑振铎信中说:“至于为青年着想的普及版,我以为印明本插画是不够的,因为明人所作的图……一到古衣冠,也还是靠不住,武梁祠画像中之商周时故事画,大约也如此。或者,不如(一)选取汉石刻中画像清晰者……加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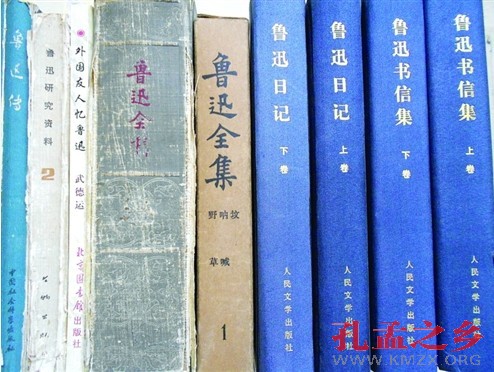
印行汉画像一直是鲁迅的一个心愿,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曾屡次提及。1934年3月6日,鲁迅致姚克:“汉画像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同年4月9日,鲁迅致姚克:“汉唐画像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数年来收集之工,亦殊可惜。但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不过无论如何,此事终当了之”。同年6月9日,鲁迅致台静农:“对于印图,尚有二小野心,一,拟印德国版画集,此事不难,只要有印费即可。二,即印汉至唐画像,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而著手则大不易。五六年前,所收不可谓少,而颇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画像……等,虽具有,而不中用;后来出土之拓片,则皆无之……兄不知能代我补收否?即一面收新拓,一面则觅旧拓……虽重出不妨,可选其较精者付印也”。同年6月18日,鲁迅致台静农:“我之目的,(一)武梁祠,孝堂山二种,欲得旧拓,其佳者即不全亦可……”“济南图书馆所藏石,昔在朝时,曾得拓本少许;闻近五六年中,又有新发见而搜集者不少……兄可否托一机关中人,如在大学或图书馆者,代为发函购置,实为德便”。
待到了1935年,鲁迅在5月14日致台静农的信中却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收集画像事,拟暂作一结束,因年来精神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劳,亦无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今乃知老境催人,其可怕如此”。同年11月15日,鲁迅致台静农:“我陆续收得汉石画像一箧,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使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崖;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后又欲选其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划又较明晰者,为选集,但亦未实行”。在同一信中又说:“印行汉画,读者不多,欲不赔本,恐难。……而需巨款则又一问题”。终因战事吃紧、物价飞涨、环境险恶、疾病缠身等原因而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