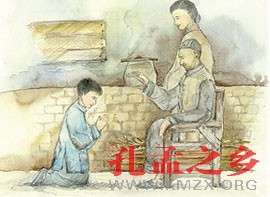帮父母做家务,给父母洗脚等体现个人的私德。用公权力去干预私道德,一般不会起到好结果;传统中国用儒家礼教治理,本质是为了专制皇权的需要。官德评价机制不完善,曲意奉承者反而飞黄腾达,从而鼓励不道德行为的存在和蔓延。
先贤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最近决定要打造“彬彬有礼”道德城市,形成以“爱”为核心的社会风尚;以“诚”为核心的职业操守;以“孝”为核心的家庭美德和以“仁”为核心的个人品质,以为这样就不会辱没作为孔子故里的名声。“彬彬有礼”道德城市涉及的范围很广,我不准备一一谈及,重点讲讲对官员的孝道要求。曲阜市委书记李长胜在10月22日的动员大会上表示,要将孝道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红线”,不孝者不得提拔重用!
且看曲阜对官员孝道的要求:每周帮父母做一次家务;每月带父母理一次发,给父母洗一次脚;每年给父母的生活费用不少于月平均工资或收入……省略号后还有其他规定,就不一一列举。
如今道德之不彰,有目共睹。曲阜作为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发祥地,素有“文明之乡、礼仪之邦”的美誉,它本来就该是个道德高地,但连它也要打造“彬彬有礼”的道德城市,可见这些年我国的道德危机到何等程度。不过,曲阜能够意识到道德丧失的危害,而行动起来,暂且先不讲他做得对与否,从积极的角度看,有这种危机感,总归是好事。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讲,用孝来治理城市尤其是官员,则开错了药方。因为这一招孔子在2500年前就使用过。孔子带领他的72门生周游天下,推销其“克己复礼”主张,但终究无人理他。他所生活的春秋战国也没有回到他推崇的“周礼”上去,而是“礼崩乐坏”了。
孔子既然做不到,今天要用孝或者礼来挽救败落的人心,拯救社会道德,更不可能。但我们的一些地方官却热衷于搞这个。除曲阜外,我所知道的还有河北魏县——所谓“孔融让梨”的发生地、四川彭山等。前者提出“德孝治县”,把孝敬父母写入县委常委会建设的文件中,明确作为县委常委行为准则中的一条。后者考察领导干部的德时,要求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乃至小区物管意见。如果说,这些都是小地方,北京则在今年出版了一套《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包括《史说官德》、《大道官德》、《为官史鉴》、《申论官德》四本,要全市领导干部学习这套丛书,作为官德建设和反腐败的教材。
固然细微处见一个人的品德,但这话也不全对。难道不给父母洗脚,不带父母理发就不是孝顺儿女和合格干部了?将儒家礼教的一套规范简化为一条条具体的生活细节的规定,用来约束官员,并同升迁挂起钩来,与其说是张扬孝道,不如说是绑架官员,是提升不了官员“美”德的。因为,孝在这里能不能起作用,它首先面临的难题是,谁来监督,如何执行?类似每周帮父母做一次家务,每月带父母理一次发,给父母洗一次脚,每年给父母的生活费用不少于月平均工资或收入,完全是属于个人私域中的事情,它体现的是个人的私德。如果我不做难道你还跑到我家去监督不成?因此,它很难动用公权力去监督执行,而没有强有力的监督,这样的规定多半会落空。当然,也可以把监督权交给家里的老人和家人,但如果家人严格执行,这其实是鼓励家人告密,是在撕裂亲情,此本身就有违儒家的规范,现实当然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因为天底下不会有哪个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而向组织揭发他没有孝敬自己?除非这个儿子是个十足的坏蛋。剩下的可能就是微服私访,但微服私访的监督效果也不会很大。总之,用公权力去干预私道德,一般都不会起到什么好结果。
礼教之不能救道德与官员,更在于整个时代的大环境与礼教盛行的传统社会截然不同。传统中国所以要用儒家的礼教那一套来治理,本质是为了专制皇权的需要。皇权为了维护自己家天下的统治,需要一套能让臣民内心信服的价值和制度来规范社会秩序,而礼教正符合皇权的要求。礼是道德的标准、教化的手段、是非的准则,是政治关系和人伦关系的分位体系,礼有威严的功能,也有亲和的作用。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克己复礼为仁”,“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等级、差序、服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显然,这套东西已不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需要的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发展,民主的讨论。倘若讲,将礼背后所蕴含的等级秩序的内容抽去,而只保留礼仪的形式,在我们目前尚有可取的话,如果想恢复古制,用礼来治理社会,规范人心,断不可行。
此外,强制官员行孝,还会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人为制造一个道德判官。传统中国最高的道德判官是皇帝,皇帝是天子,代天来管理人间,所以儒家假定皇帝是一个在道德上完美无瑕的人,他有资格来教导臣民。实际情形自然不是这样,所以即使在古代,官场伪善之风也盛行。如今是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也就没有道德的权威,谁也不敢说自己的道德就一定完美,比别人高,这时候,要判断人的道德的高下,就只能依赖权力,谁的官衔大,权力大,谁就有资格做道德判官。所以,它最终还是和权力挂上了钩。这不能不是一种讽刺。
可见,用孝来治官,结果是不会好的。其实,中国两千多来年的礼教历史对此做了否定回答。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官员道德的腐败当然需要拯救,但不能靠孝道、靠复礼来进行。官员道德的沉沦有很多原因,关键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市场经济的实行使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进了权力领域,官员把人民赋予自己管理社会的权力变成一种“奇获可居”的商品,用它出售来交换利益;二是政治运作的制度化和法治化程度低,政务不够透明和公开,致使官员在运用权力时,更多是靠道德良心制约自己的行为,缺少严格的制度规制人们的行为,从而使得官员的道德失范不可避免。三是现有的官德评价机制不完善,公正、守法、为民者得不到重用,曲意奉承者却反而能够飞黄腾达,从而导致官员队伍“劣币驱逐良币”的发生,鼓励不道德行为的存在和蔓延。
所以,拯救官员道德,应该放在加强对政府行政行为的道德审视,增强行政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发展公民意识,发挥民主和舆论的监督等方面。官德考评需要,但必须把重点放在法的建设上,用法而不是孝来约束官员。传统中国之所以发展不出西方意义上法治,根源在于儒家用礼来代替法制的建设,或者干脆将礼入法,作为惩罚的手段。而礼着眼的是人们的伦理要求,规范的是人际关系,中国人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耗费在如何设置复杂烦琐的的礼仪上,耗费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这导致中国的礼仪文化发达,而科学、民主与法治落后。强化法治、加强对官德的立法才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正途。
邓聿文为资深媒体人、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