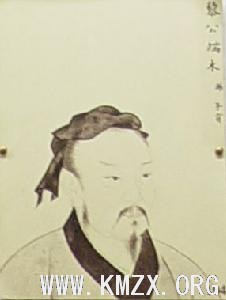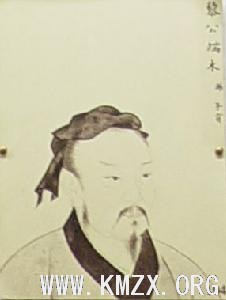
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
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子贡学绩上优异。《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据
《左传》,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
《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
《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
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具体而言就是:存鲁,乱齐,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
子路、
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从
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
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
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
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
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虚。《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端木赐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子贡:中华儒商鼻祖
“儒商”,一个高雅动听、令人赞羡的称谓,只有以儒学为根基、以诚信为准则、奉行“富而好行其德”的成功商人,才配享此美誉,例如春秋后期的陶朱公范蠡,历代晋商、徽商中的佼佼者。追溯中华儒商的渊源,其始祖应是两千多年前的孔门高足──端木子贡。
子贡(公元前520─前456年),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子贡小孔子31岁,17岁拜孔子为师,深得孔子真谛和儒学精髓,誉为“孔门十哲”之一。子贡出生于商业世家,对经商有先天优势,加上经常跟孔子周游列国,得以开拓视野,这也为其以后打拚奠定良好基础。子贡老家在河南省鹤壁市浚县,鹤壁因“古有仙鹤游云淇水,栖之南山陡壁”而得名。这里苍山莽莽、淇水悠悠,自古为钟灵毓秀之处,不仅引来无数雅士鸿儒,也造就了商贸繁盛的黄金码头。浚县大蔪山、浮丘山上至今留有吕祖祠、禹王庙、天宁寺、观音洞等人文古迹。
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在煌煌巨着《史记》中,记载亚圣孟子仅用215个字,而写子贡却用了5000字。足见这位大史学家对子贡推崇之深。清代浚县县令刘德新曾多次拜谒子贡祠,非常敬仰这位儒学先进,并撰诗《谒黎公祠》云:“曾作素王奔走臣,六瑚四琏擅名珍。分庭能抗诸侯贵,结驷不骄处士贫。事鲁只因从鲁叟,封黎原本是黎人。淇园此日无余竹,古木犹然拱泗鈠。”不啻赞颂子贡精通六艺的才学和能言善辩的风采,也讴歌了子贡作为“跨国企业”掌门人罕见的经商头脑。
跋涉于大蔪山与淇水之间,在历史的长河里逆水而上,追寻这位儒商鼻祖的人生轨迹。元宋时代,人们一直把大蔪山南麓的荒丘当作子贡墓来祭拜,附近的子贡祠也越建越大。直至明万历年间,浚县县令宁时馍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才在距县城数里外的张庄找到真正的子贡墓,于是上报郡台、平掉假墓,将子贡石像移回张庄,在原址重建墓祠,并立《改正先贤黎公墓祠记》碑,以记其事。
由张庄东北走十几分钟,见一片杨树林傲立旷野,秋风中飒飒作响,显得苍茫而静穆。再拐上一段羊肠土路,花生地中伫立着一块石坊,赫然刻着“子贡墓”三字,再穿过一片玉米地,终于见到那块“劫后余生”的《改正先贤黎公墓祠记》石碑。碑高约四米、宽一米,上镌当年浚县县令宁时馍昭告天下确定子贡墓在张庄的碑文。石碑后凸立着一个高七八米的土丘,这便是子贡墓了。子贡祖宅在县城,缘何下葬距城七八里外的张庄?想必源于“风水”吧。我观之,张庄居高临下,三面环水,位居“龙虎堤”之首,后人为他选择了“龙头”作为长眠之地。
在端木故里,深为这位杰出的古代思想家、纵横家,又潜心经商之术、终成中华儒商鼻祖而感慨。当吴越大军远征北方,吴王夫差强征丝棉以御寒,使丝棉紧缺价格走高。聪敏的子贡便抓住商机,从各国收购丝棉到吴国贩卖,这一“价格差”让他捞得“第一桶金”。后来为追忆先师懿德,心灵手巧的子贡用木头雕刻出孔子像,前来祭拜的将相诸侯见状都想拥有一个作纪念,子贡又从中看到无限商机,招募工匠大批生产孔子雕像,又大赚了一把。子贡还首开了“跨国公司”之先河。据《史记》记载,他“鬻财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他发现各国权贵皆以佩戴珠宝为时尚,就大量制造贵重佩饰搞“跨国营销”,赢得盆满钵满。
子贡的儒商美誉来自诚信。他虽做买卖,却不忘儒家学说;他家财万贯,却富而不骄、富而有仁。《吕氏春秋》记述了子贡自己出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可谓千古流芳。他积极牢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坚持以诚待人、诚信交易。《论语》多处记载子贡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他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没有“信”一切就荡然无存,更遑论发财乎?是“言必信、行必果”使子贡立于不败之地,达到“忆则屡中”、“义利双赢”的最高经商境界。由于他名满天下,到邻国经商各国君主都会礼貌地会见他,说明他真是名副其实的商业钜子了。
孔子对子贡十分看重,称他“始可与言《诗》已矣”,赞他对孔学达到心领神会的地步。子贡靠经商积累大量财富,为孔子及其门生周游列国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堪称以文促商、以商养文的成功典范。孔子对此评价甚高,《论语.先进》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说颜回在道德上很完美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子贡却不安现状,亲自做生意,极善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准。孔子云:“富而可求,虽执鞭之人,吾亦为之;如不能求,但随吾所好。”可见圣人并非不爱财,只是“取之有道”罢了。浚县不少商场可见“子贡经商取利不忘义,孟轲传教欲富必先仁”的对联,足见故乡人对先祖和孔孟之道的敬重。
#p#副标题#e#
沧海桑田世事更迭,想不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一代儒商鼻祖子贡重新唤起人们的关注。毕竟,儒商在中华崛起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难怪沃尔玛公司创始人也会说:“沃尔玛最初灵感来自中国古老商号──端木子贡!” (马承钧)
[NextPage子贡:孔门中的“成功人士”]
子贡:孔门中的“成功人士”
子贡,姓端沐(木),名赐。子贡是卫国人,年少于孔子31岁,他成为孔门弟子,当是在孔子携门徒客居卫国的时候。
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智商最高,然而,却从未得到孔子对颜回那样的赞赏。有一次,孔子有意问子贡:“你和颜回哪个更强些?”子贡说:“我怎么敢跟颜回相比,他是闻一知十,我是闻一知二。”夫子赞同说:“你是不如他。”子贡这么回答,与其说是自知之明,毋宁说他很聪明,他知道颜回是夫子的最爱,也明白夫子这么问的意思,倘若他不表明自甘于颜回之下(而且差距很大),一定会让夫子不开心,还可能自讨没趣。
从《论语》记述可知,子贡经常受到夫子的抑揄,如:“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有时臧否他人,夫子说:“你自己有多好吗?我就没这个闲工夫。”又如:“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子贡问夫子,我这人怎么样?夫子说,你好比是器物,那种盛黍稷的瑚琏器物。夫子说过“君子不器”,可知夫子把子贡比作瑚琏之器,实在是个不高的评价(连君子都够不上)。另外据《孔子家语》所记,孔子晚年时还说过:“吾死之后,则商也日益,赐也日损。”——预言自己死后,子游会日益进步,子贡将日趋不行,其理由是:子夏喜好与贤良的人相处,而子贡则爱跟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前者如入芝兰之室,后者如入鲍鱼之肆,因此便有相反的结果。不过,这个段子是否属实,似有可疑之处。
当然,夫子对子贡的称赞也是有的。比如,夫子曾对季康子说:“赐也达,于从政何有?”——子贡通达事理,从政对他来说是绰绰有余。又如,有一次在谈到贫富的态度时,子贡引用《诗》里的句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子便高兴地称许他“告诸往而知来者”(即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这些都是对子贡才智的赞赏。其实,子贡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有点怀疑精神,这见诸《论语》的一则记述:“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周室“伐纣”而得天下,商纣王作为前朝“暴君”,于是被彻底妖魔化,且成为天下“共识”。然而,子贡却怀疑这种主流“共识”,认为纣的恶未必像人们说的那么厉害,并由此推断:君子要是“居下流”(即处于下风、失势的境地),天下所有的坏名声都会落到他的头上。子贡这种质疑性的见解,在当时无疑是独到而犀利的。从《论语》记述来看,子贡这番话没有当着夫子的面说,若是夫子闻知,也不知道他是表示赞同呢,还是厉言申斥。但有一点似可以肯定,这种有违主流“共识”的怀疑之论,谨守“非礼勿言”的颜回是说不出,甚至想也不敢想的。
子贡以擅于“言语”,列为孔门“十哲”之一。但我们知道,孔子对巧于言辞总不怎么欣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子贡的伶牙利齿、能言善辩,经常会被夫子驳斥。不过,在外交场合和关键时刻,子贡的“利口巧辞”就派得上大用场。据《仲尼弟子列传》记述,齐国的权臣田常(即陈恒)蓄意攻伐鲁国,孔子对弟子们说,国家面临危难,你们何不出来效力呢?子路、子张等请缨,夫子没有应允;子贡请求出马,夫子当即就同意了。于是,子贡先到齐国,挑唆田常攻伐吴国,随后又到吴国,鼓动吴王去攻打齐国,然后再去越国,对越王说吴王的坏话,最后来到晋国,说吴王有野心,让晋君做好抵御吴军进犯的准备。……子贡以其“利口巧辞”进行游说,在诸国之间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结果吴军果然与齐军交战,吴军战胜后又兵临晋国,却被以逸待劳的晋军击败,越军乘机侵袭吴国,最终吴王夫差被杀,吴国灭亡,越国由此称霸。这就是所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利口”的杀伤力竟有如此之大!
《孔子家语》亦有类似的记述,而且还有孔子在事后的评说:“夫使乱齐存鲁,吾之始愿。若能强晋以弊吴,使吴灭亡而越霸者,赐之说也。美言伤信,慎言哉。”——使齐国乱了作战计划,从而保存了鲁国,这是夫子原来的意愿,而让晋国加强,吴国灭亡,越国称霸,这些都是子贡游说的结果。夫子认为,子贡“说”得太过火,伤害了信义。
然而,《仲尼弟子列传》和《孔子家语》的这些记述,是没有史实依据,不可置信的。吴王夫差自杀,吴国灭亡,是在公元前473年,此时距孔子离世已6年,即此一端就可证其无稽之说。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贡所占的篇幅最长,而其中子贡在各国的游说词便占了约五分之四,由此可以看出,太史公司马迁对游说之词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偏好——如苏秦及张仪的列传,同样也大量引述其游说词——不过,子贡的那些游说词从何而来,也很令人怀疑,似不能排除“创作”的可能性。
将子贡当作纵横家祖师爷的描述,虽然不可信,但子贡巧辞善辩和杰出的外交才能,则是确实无疑的。据《左传》记载,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吴王派太宰嚭要求鲁国重温过去的盟约,鲁哀公认为此举可能别有企图,便派遣子贡去婉言拒绝;子贡奉命前往,一番有理有节的话,说得太宰嚭无言以对,重温盟约的事就此作罢。同年,卫侯在吴国会见吴王,谢绝和吴国结盟的要求,吴王于是派兵包围了卫侯的馆舍;当时作为鲁国随行使者的子贡又奉命前往斡旋,子贡带了丝锦去拜见太宰嚭,抓住吴国欲称霸于诸侯的企图,指明围困拘禁卫侯的严重后果,说得太宰嚭心服口服,于是卫侯很快得以解围归国。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鲁国与齐国媾和,子贡作为副使来到齐国。陈成子(即田常)在宾馆会见鲁国使者,宣称齐国会像对待卫国一样,也友好地对待鲁国。正使子服景伯揖请子贡陈言应对,子贡便上前从容地说,这正是鲁君所期望的,接着话锋一转,提起吴国进犯鲁国时,齐国趁机侵占鲁国的土地,若比照齐国跟卫国处理类似问题的前例,鲁国也应得到相等的对待。这一席话让陈成子自感理亏,不久齐国就把成邑归还给鲁国。以上诸例,足以显示子贡能言善辩、机智敏捷、外交中不辱使命的卓然风采。
子贡还是经商的高手。《论语》中记道:“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将颜回和子贡做对比,前者安守本分,穷得丁当响,后者不安于命,做起生意来,却屡测屡中。夫子在这里有所感慨,但并没有赞赏子贡善于经商的意思。“士、农、工、商”,位于四民之末的“商”,为儒家所轻视。当然,夫子也没有特别阻止子贡从事商业活动。按钱穆的说法:“盖子贡以外交使节往来各地,在彼积贮,在此发卖,其事轻而易举,非若专为商贾之务于籴贱贩贵也。”可谓是亦官亦商两不误(不过,子贡的买进卖出,须有准确的商业判断力,以及足够的风险意识,恐怕并非如钱氏说的“其事轻而易举”)。子贡的生意越做越大,以至于“家累千金”。据《史记·货殖列传》说,“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在孔门之中,子贡无疑是“成功人士”,也可以称为中国“儒商”第一人。
由于忙碌于外交事务和商业活动,子贡后来不能常侍于夫子身边。当他闻知夫子病重,匆匆赶来谒见时,夫子正拄着拐杖徘徊在门口,一看到子贡,夫子就问:“赐,汝来何其晚也?”可知夫子当时急待的心情。颜回、子路相继离世之后,子贡在夫子心中便是最倚重的弟子了。夫子伤感地对子贡说,他昨晚做了个梦,自己坐在东阶和西阶的两柱之间,夏人死后停棺在东阶,周人死后在西阶,殷人则在两柱之间,我是殷人的后代呵!……七天之后,夫子便怀着“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的遗憾,溘然离开了人世。这七天,子贡朝夕守候在夫子身边。
为夫子主持安葬之礼的,想必也是子贡,这从孟子谓“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一语,即可推知;于此还证示:在当时的众门徒眼里,子贡威望是最高的。弟子们各自离开之后,子贡在夫子墓旁筑了一间小屋,又在那儿独自守丧三年。前后六年,子贡就这样守着夫子的亡灵,将公务、商务和个人的名利全然置之度外。
孔子活着的时候,虽然对子贡时有抑揄,但子贡却从未有何不满,或像率直的子路那样顶撞夫子,更没有因自己的能耐和成功,在夫子面前稍显骄矜之色。聪明的子贡很会做人,如我们在《论语》里看到的,他总是对人称道夫子。夫子亡故之后,有人以子贡的出众才华和成功名望,夸他“贤于仲尼”,或以此来诋毁孔子,子贡不予认同,说夫子之墙数仞,一般人不得其门而入,自己不过是及肩的低墙罢了;还把夫子比作日月,是不可逾越,也不可毁伤的。……子贡就是这样旗帜鲜明,捍卫着夫子的声誉。不仅如此,子贡在作为使者或富商访问各国君主时,总不忘在他们面前对孔子大加宣扬,《货殖列传》因此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有像子贡这样的忠诚弟子,可以说这正是孔子作为人师的最大成功。(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