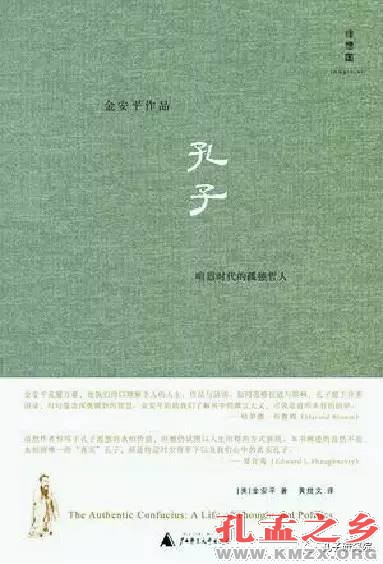
我们为什么如此的关注孔子呢?因为“直到20世纪中叶为止,中国与孔子的观念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自我与人伦概念,以及文化与历史建构,似乎全发轫于孔子个人的心灵。”对于西方世界,“将中国的一切的好事坏事全归因于孔子。” 是什么造就了孔子的“卓然不群”?在她看来,孔子有三项特质:“学而不倦,对陶铸完美人格的渴望,以及积极在此实践自我”。这也是她写作的主线。
金安平首先提到,在邹城访问期间与高中生的对话。这种倒叙手法在讲故事中常见,这在美国中国学的一些学者中也是常用的手法,金女士的丈夫史景迁对此更为娴熟。在概述了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孔子的态度演变后,金安平进入对孔子历史世界的认识。
关于孔子早年的记录实在是太少了,因此,金安平开始就是从孔子“去鲁”的举动讲述的。孔子为什么突然辞官周游列国?她揭示出《论语》、《孟子》、《史记》记载中的相互矛盾之处,然后以《春秋》以及《左传》记载的鲁国内乱入手,指出孔子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她看来,在孔子担任司寇前,早有和家臣合作驱逐三桓的意图,当然这一切因为他担任司寇发生了改变。而且在齐鲁会盟期间,孔子的表现显然得罪了齐人。金安平还提到孔子个人的一些情况,如双亲离世,婚姻结束,女儿长大等等因素,这些都对孔子决心离开鲁国起到促进作用。
孔子的这种使命感以及和他的学说之间的关系,金安平将其放在春秋时代鲁国的具体社会政治现实中加以考察。作为卿大夫的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自然向往周公的礼乐秩序和谐的社会。
孔子离开“鲁国”后,开始了大家熟悉的“周游列国”。在此期间,他的弟子们时刻跟随着他。孔子在与弟子们的对话中,不断支持、提升着自己的信念。在金安平看来,孔子经常谈话的弟子是宰我和子贡。因为宰我喜欢辩论,而子贡则条理清晰。其次是颜回和子路。
对于孔子周游列国的描述,金安平尽管认为许多地方需要靠史学家的历史想象,但她还是根据现存的史料进行了自己的解说。在这些材料中,她认为庄子记述较为准确,加上《论语》的记载,孔子实际到过卫、宋、陈、蔡、楚五国。她认为,并非孔子每次出国,都算在周游列国的行列。比如孔子去过齐国,但时间要晚。孔子第一站去的是卫国。因为“鲁、卫之政,兄弟也”。其中,孔子见南子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她分析了孔子见南子的心理状态,即是钱穆所提出的孔子急于觅得官职。对于孔子在卫国求仕的情况,金女士用很大篇幅进行了解释。这自然也涉及到孔子如何认识和评价女人的问题。金女士不赞同司马迁的写法,因为春秋时代也有远见卓识的女性,如定姜。但孔子认为女性一旦与男性智慧相当,就不是女性了。孔子离开卫国,在宋国遇到了众所周知的暴力事件,司马迁的描述显然不可信,孟子的版本相对可信,也就是“孔子已经预知有危险,于是预作提防,微服而行。”(中文版,第122页)至于将阳虎与孔子此事关联起来,并不可信,但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故事的精彩程度比较有兴趣。离开宋国,孔子在陈国住了约三年,对于陈蔡之厄,《论语》、《荀子》、《庄子》的记载各有不同。在此基础上,司马迁进行创作,演绎了他心中的故事,金女士进行了详细分析。
孔子返鲁是多种原因促成的。金安平认为主要是因为冉求和子贡在鲁国的努力,加上当年反对孔子的鲁定公和季桓子已经逝世等。孔子结束周游列国的生涯,返回鲁国后,与季孙氏在是否应该向封地的佃户抽取土地税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也导致孔子对冉求的不满。金安平认为,这一时期孔子的政治影响力是有限的。如他觐见哀公、求见三桓等基本上是徒劳无功。也因为此,孔子开始将注意力转入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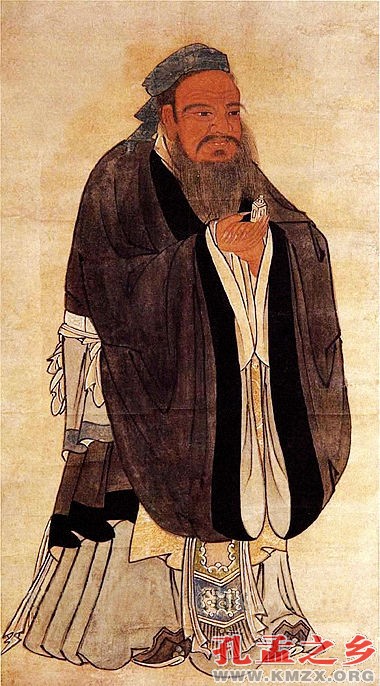
对于孔子作为教师职业的分析,金安平的分析很有见地。孔子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但并不愿意接受老师这个头衔。子贡和冉求在政治上的成功为孔子的教学事业树立了典范。“孔子所做的正是他自己认为不可能或不适切的事:他成了一个老师。”(中文版,第168页)金安平发现,在教学中,孔子使用最多的字是“诲”,很少使用“教”,没有使用“训”。因为“教”是不平等的关系,而“训”则体现出研究的意味。孔子传授的内容是古老的诗书礼乐知识,但这些孔子是经过思考精炼过的。除礼制外,“音乐”是个能使国家“直道而行”的影响源。在孔子看来,音乐是文化的极致。孟子认为,孔子能顺应时势,如集大成般,“金声而玉振之”。这里的“顺应时势”与“权宜行事”的区别在于“人们是否真的致力于学习”(第178页)。金安平指出孔子对“乡原”的怀疑,即:“乡原,德之贼也。”从这个观点出发,她重新分析了孔子诛少正卯一事。正是从此意义上,金女士认为:“少正卯是孔子最顽强的敌人”。以孔子对人命的重视,杀少正卯一定是再三判断的结果。
孔子注重礼仪,尤其是生死之礼。如丧礼的各个环节:“礼仪、情感以及丧礼呈现的哀悼者真实面貌。”(第204页)孔子很少压抑自己的情感,他为母亲服丧三年后,弹琴都不成曲调。在颜回死后,格外的哀恸。不仅如此,即使对狗,也给予适当的葬礼。
孔子葬礼后,孔门弟子就谁能继承孔子的精神衣钵产生了分歧。因为他们把孔子提升到了崇高的地位,无论哪个弟子都难于逾越。直到孟、荀的出现,孟子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金安平从两者思想中看出了继承和发展。其中,孟子最大的发展就是人性观(中文版,第223页)。孔子的另外一个追随者是荀子,他猛烈批判了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偏离”。金女士认为,荀子的学说“也让统治者与大臣能随时针对当前局势做出调整”,荀子着重考虑心的知性潜质,而非情感潜质。他还添入了“周公”,构建了“大儒”概念。孟子和荀子在死后的命运不同,孟子在经过宋代理学大兴后备受喜爱,而荀子则逐渐受到贬抑。最后,金安平又回到了现代时空,通过对比今天孟庙和荀庙截然不同的景象,展示了孔子思想不同发展方向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影响。
读罢此书,深感金安平的《孔子》确实发人深省。她采用“去圣化”手法,考证严谨,评论公允,不是为了媚俗故做惊人之语,也不诋毁曲解或盲目推崇他的思想,正因为此,却更凸显出孔子的伟大,这一点与“百家讲坛”于丹版的《论语心得》区别较大。
此书在美国获得广泛的认可,耶鲁大学人文科学史特林讲座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金安平克服万难,使我们得以理解圣人的人生、作品与话语。如同苏格拉底与耶稣,孔子留下许多语录,句句蕴含深奥微妙的智慧。金安平协助我们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可说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见中文版扉页) 芝加哥大学中国古史研究教授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说道:“虽然作者惊叹于孔子思想的永恒价值,但她仍试图以人生历程的方式展现。本书阐述的虽然不是永恒而唯一的‘真实’孔子,却是特定时空背景下以及我们心中的真实孔子。”(见中文版扉页)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赞叹说:“两千五百多年来,孔子的学说并未因政治动荡与野蛮压制而消亡,反而更加昌盛。金安平长年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断简残编,描绘出一幅极为可读且发人深省的孔子人生时代肖像。”(见出版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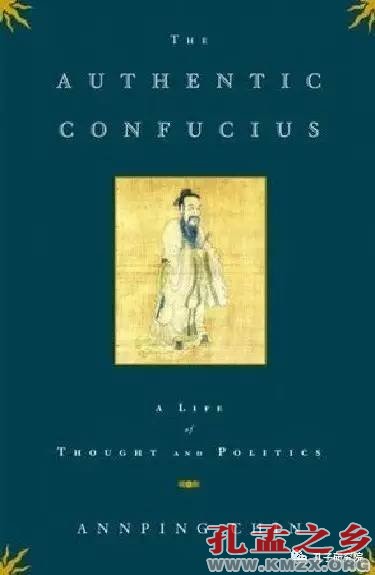
最后,从翻译角度看,中文版由台湾专职译者黄煜文翻译,译文可谓优美。但也不是完美无缺,比如中文序言开始的第一段:“孔子不仅对人生全力以赴,也戮力参透其中义理。他希望‘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学而不倦,对陶铸完美人格的渴望,以及积极在此世实践自我,正是这三项特质造就了孔子的卓然不群。或许当时还有其他人也追寻着与孔子相同的目标,但没有人的渴望像孔子一样强烈,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决意搜罗从古到今的一切知识——历史、诗歌、礼仪与音乐,以理解人性与人类命运的本质及不变的成分,并使自己‘无大过矣’”。 若比较其原文,则不难发现有信息的遗漏问题,如“an awareness that this life was the only occasion he had”,在中文翻译中并未体现。还有一些因一些较为俗词,使得原文的内涵未能充分体现。如上文提到的“参透……义理”、“陶铸完美人格”、“卓然不群”等词语,原文则为“Confucius concentrated on living life as well as he knew how. He wished only to be granted a few more years so that, he said, “when I reach the age of fifty, I may try 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s of change and I shall be able to steer clear of making serious mistakes.” It was learning, therefore, and a desire to perfect himself, together with an awareness that this life was the only occasion he had to fulfill his wish and promise, that distinguished him.”
显然,原文中通过简词淡笔,让我们既感觉到孔子的不凡,又感觉到孔子与众生相通的人性,中文用词却将孔子推向了神坛。当然也许是译者为了配合来自古籍的引文,不自觉地尽量使用现成语,来制造“典雅”的效果。但如果达意都做不到,“典雅”何用?也许这里有点苛刻,但《春秋》责备于贤者,这也算是对目前国内文史翻译者的一点激励吧。
(作者路则权,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