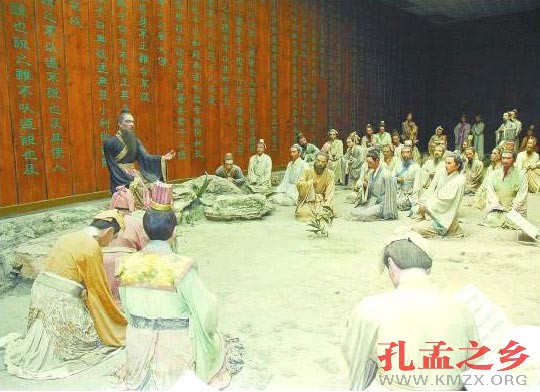【核心提示】孔子已走投无路,他在《卫操》中写道“周道衰微,礼乐凌迟。文武既坠,吾将焉归?周游天下,靡邦可依”!既然文明礼仪不能带来“有道”的仁政德治,索性居夷浮海,逃至蛮荒之地。兴许,那里正是“孔颜乐处”。
《论语》中“子欲居九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两章颇为费解。其分别出自《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曾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可知这两章所记绝非“戏言”,明确透露孔子晚年意欲避世。
孔子十分注重对周礼的传承发扬。他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充分肯定管仲的尊王攘夷思想,《论语·宪问》载“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八佾》还记“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先进的华夏民族,必须防止被“被发左衽”的落后部族同化,孔子的这种夷夏之辨思想,已表述得十分明确,他以实际行动捍卫了周代文明。
既然如此,孔子何以“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呢?对此,历代注家只作了字面注释,缺乏综合分析,不可不辨。
两章内容为一事两记
在今本《论语》中,这两章分属不同篇次。其记孔子将要前往的一为“九夷”,一为“海”,但其性质和主题完全一致,实为一事两记。
许慎《说文解字》把这两章合在一起解说:“东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汉书·地理志》亦记:“孔子悼道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朱熹《论语集注》卷5断言:“东方之夷有九种。‘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清代刘宝楠更坚称:“子‘欲居九夷’与‘乘桴浮海’,皆谓朝鲜。”理应视为同一章进行分析。
“夷”泛指东方土著族群。此之“九夷”,《汉书》卷28《地理志》、颜师古《汉书注》、《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及其《东夷传论》均指朝鲜半岛。但是,这种推测缺乏必要论据。还有人主张“九夷”指“淮夷”(淮河下游地区,今安徽、江苏两省中北部)。这一地区原属鲁国,后沦为吴、楚两国战场。而孔子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坚信“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这一观点也不可靠。
清代翟灏《四书考异》记:“罗泌《国名记》引《逸论语》:‘子欲居九夷,从凤游。’魏武帝诗曰:‘子欲适西戎。’欧阳建诗:‘子欲居九蛮。’”可知,“九夷”,并非确指某一地区,未必是指东方,可能指“东夷”,也可能是“南蛮”、“西戎”。总之,“九夷”泛指荒凉遥远、文化落后的“化外”之域。
明确这两章的具体年代,无疑是确知其真实含义的重要条件。其时间上限,应是孔子返鲁之后。刘宝楠推断说:“夫子本欲行道于鲁,鲁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国,最后乃如楚……至楚,又不见用,始不得以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记·孔子世家》虽未载‘浮海’及‘居九夷’二语,为在周游之后,然以意测之当是也。”孔子返鲁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岁末。时间下限不会晚于哀公十五年的子路之死,而子路在一年前就离开了鲁国。由此可证,《论语》“子欲居九夷”等两章所记之事,必定发生在鲁哀公十二年至十四年春的两年间。
居夷浮海计划无果而终
孔子决意“避世”到“九夷”或“海”上,但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谁能与他同行?他首先想到的是子路:“从我者,其由与!”然而,子路仓促出逃,迫使孔子中断这个计划。而子路之死,使孔子一病不起,《史记·孔子世家》“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后七日卒”。
在《论语》中,可以清晰看出孔子思想的前后变化。《阳货》记:“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与他早年“知其不可而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进取精神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论语》早已埋下了“伏笔”。《泰伯》记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宪问》记“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孔子把隐者分为四个层次,“辟地”、“辟色”、“辟言”三者在孔子周游列国时就是日常生活,而结果竟是“干七十余君无所遇”。眼下,辟世成了唯一选择。《微子》记桀溺对子路所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且而(尔)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真可谓一语成谶!
《述而》记“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岂是寻常之语!恰恰印证了孔子已认识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再造东周”的名山事业难以实现。14年前,因鲁国君臣荒政,孔子愤而出国远游,终于在迟暮之年回到父母之邦。而14年后,鲁国除了定公换成了哀公,执政大夫由季桓子改为季康子,昔日“君不君,臣不臣”的政治情势愈演愈烈,季孙氏“八佾舞于庭”,公然在自家庭院演出天子乐舞,还有什么残忍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再者,孔子返鲁之时,国内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当政者却施行“田赋”,加重人民负担。冉有帮助季孙氏暴敛民财,使孔子十分愤怒。《论语·先进》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有位居孔门四科“政事”之首,政治才干最为优秀。但冉有令孔子大失所望,这是迫使孔子决意再度出游的又一原因。
综观孔子所周游列国,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姬姓封国:卫、曹、郑、蔡;第二类是先代遗民封国:陈(虞舜遗民封国)、杞(夏遗民封国)、宋(殷遗民封国);第三类是“另类”的楚国。而这三类国家都未能任用孔子。
孔子已走投无路,他在《卫操》中写道“周道衰微,礼乐凌迟。文武既坠,吾将焉归?周游天下,靡邦可依”!既然文明礼仪不能带来“有道”的仁政德治,索性居夷浮海,逃至蛮荒之地。兴许,那里正是“孔颜乐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