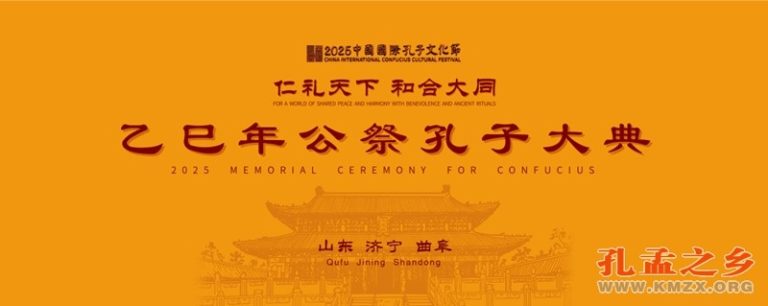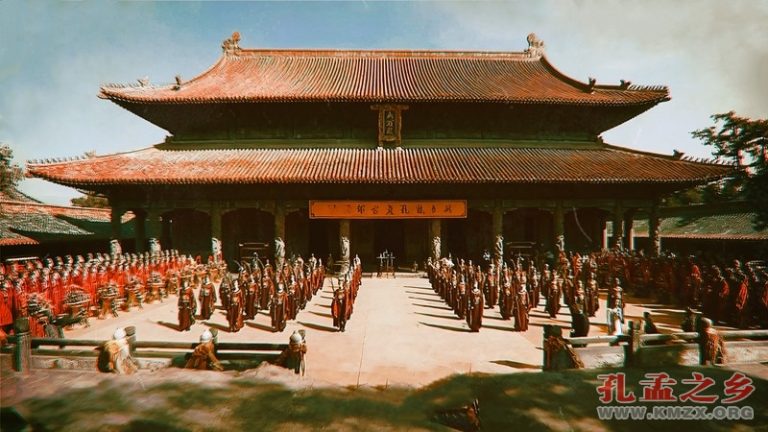经过了艰苦而又略嫌漫长的蓄势过程,济宁的文学创作终于迎来了它的起飞时期。我们不能漠视这个来之不易的起飞。这次起飞以及由这次起飞所带来的成熟的作家与成熟的作品,将会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支生力军,为民族的精神宝库留下耐磨的产品,并将对济宁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个整齐的作家队伍开始出现
我们济宁当然有全国性的当代著名作家,如词作家乔羽、评论家孔范今、当代山水诗的开创者孔孚、诗人郭路生(笔名食指)等,但是他们的成长与成就都是在离开济宁之后获得的,在这篇文章中就不再论述。
从1978年之后的二十年间,济宁的作家队伍在山东省一直排不到重要位置,也鲜有在全国叫响的作家与作品。吴延科、邵建明、姜葆夫、曲春礼、李贯通、王耕夫、殷允岭等作家,曾经是我们济宁作家的代表。只是到了李贯通1987年写出了他的获全国奖作品《洞天》之后,济宁的文学创作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分量。他的小说集《正是梁上燕归时》、《洞天》、《天下文章》、《天缺一角》、《李贯通小说选》等的出版,更使这种“分量”有了底气。而曲春礼的小说《孔子传》、《孟子传》、《孔尚任传》,殷允岭的长篇小说《大船浜》等的出现,则令这种“分量”得到了充实。
但是毕竟,这支队伍是不够强大、也不够齐整的。起码在散文、诗歌、文艺评论、报告文学等领域,我们还缺少真正有实力的作家。
这种状况在近十年间逐步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小说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出现了刘亚伟、陈宝旗、孙宜才、杜辉、赵学敏、田素华、韦星、张德洋、王沪城、程天翔等多位小说作者,尤其是最近几年更涌现出了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王方晨(金乡县人)、岳喜虎(梁山县人)、卢金地(兖矿集团)等三位小说家。诗歌方面,曹宇翔、王黎明(均为兖州人)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诗作,在中国诗坛占有了一席之地。纪广洋、于常印、李克实、姜良纲、王青春、姜光炎、张伟、张侗、赵霰、汪蕾等诗歌作者,都写出了各具特色的好诗篇。文艺评论上,曲师大的蔡世连等,济宁师专姜葆夫、宗元、彭兴奎,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姜葆夫出版了《古典文学论文集》,其中有关刘勰的评论有着多点创见;而他与李善奎共同编选的《常用古诗500首》,更是一版再版。宗元先生写出了专著《路遥论》和多篇有相当水准的现当代文学评论,引起了文学评论界和部分作家的关注。彭兴奎和曲阜的陈代,尤其对济宁的作家给予了关注与评说。原济宁毛织厂的职工窦洪涛则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上有着较大的收获,于《人民文学》和其他重要刊物发表了有关教育、癌症等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以小说见长的作家殷允岭,在最近几年里陆续写出了《雷锋传》、《焦裕禄传》和《孙家正传》,电视台记者周长行写出了《乔羽恋歌》、《赵忠祥》等,都是我市传记文学的重要收获。汪林、高建军则在民俗文学的创作上有着多种收获。
我市的文学创作在近十年间取得重大突破的当属散文的创作。先是有张九韶、胡昭穆、刘长岭在散文天地里的成功耕耘———张九韶先后出版了散文集《爱的湖》、《太阳味儿》,胡昭穆则写出了《走过门前一条街》等一批美文,刘长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有关微山湖的散文。而作家李木生、王开岭在散文上的努力与追求,则使济宁的散文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两人都曾以写诗出道,并创作发表了一批有着相当质量的诗歌。但是散文的创作则是他们近十年间的主要收获。他们的散文以其锐利深厚的思想性与讲究语言的艺术性,连续多年被我国众多选刊、丛书选载,开始引起中国文坛的关注。周伟、孙继泉、鲁先圣、李雁鸣等人的散文以其真挚的情感和朴实的语言,拥有着广泛的读者。与其一道,还有众多散文作者如龙鸣、刘利民、满涛、张瑞、刘红、孙瑞雪、贾向华、井传荣、胡勤贵等人,都在散文园地里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写作。
越过重重关隘才能真正腾飞
虽然起飞之势已成,但是济宁的文学创作注定还需要克服重重关隘。
而首要的关隘还是作家自身。文学创作说到底还是个体化的独立性劳动,完成任务式的大兵团作战或者集体运作等,都只能适得其反,文学作品只能从作家的心灵上流淌出来。因此,把作家自己锻造得强大起来是第一要务。试想,一个精神委琐、内心龌龊、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怎么可能制造出像样的精神产品呢?
这就需要有一颗柔软的心肠,能够感受并且理解世间的苦难与欢乐;要有一个能够独立思考且又灵敏如弦的大脑,让批判与思想的锋芒察幽烛微;要有一个宽广淡泊的胸怀,能容纳能过滤,从而给文学一个广大的生存空间。勿庸讳言,正在起飞的济宁作家群,聚集了一大批人才,是我市文化界的精英。他们不仅具有可以依赖的才能与敬业精神,也闪耀着做人的光彩。在物欲横流的时候,他们眼里还常常充满着感动的泪水,还坚守着心上的善良与独立的人格。
但是就目前济宁的作家队伍看,我们还缺少大气象的作家。我们还缺乏高远的追求,不少时候只让眼睛盯着面前的得失,随便一点诱惑,就能让我们心动一阵子。当然,作家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养家糊口,也要面对具体而又无耐的现实。但是既然我们选择了文学这个行当,就应当在我们的心里为文学撑起一个能够飞翔的空间来,而这个空间往往是需要我们学会拒绝和放弃。这也想要、那也想要,就没有工夫也没有心思去侍候文学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各人文学前途的大小,往往在于这种拒绝与放弃的程度。如果我们为了商业上的一点利益,就会将我们手中的笔“卖”掉;如果我们为了一个会员、理事之类的称号,或者为了一个虚职、一点蝇头小利,都会明争暗斗甚至争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整天为了得一个什么奖(其实当今好多煞有介事的奖,其实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而费神劳力、夜不能寐,之后便是或喜形于色或伤心沮丧;如果我们仅仅将文学当作走入仕途的敲门砖,在官场上说官话、在文学圈里说文学话,对外以文学当作“淡泊名利”的招牌,内心却无比热衷于钻营并沾沾自喜于机巧得来的一官半职;如果我们整天沉湎于酒场会场,酷嗜热闹,拒绝寂寞,我们哪里还有创作的时间与创作的心境———这样的胸怀,还怎样盛得下文学?不要说盛得下,这岂不辱没了文学?
检视我们这支队伍,也许不乏才情与热情,但是却缺少底气十足的学识与义无反顾的实干。凭着才情与热情,头三斧也许能够挥舞得有声有色。不过文学不是一时的事业,而是一生的事业,没有后劲也就没有了远大的前途。而这个后劲,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学养的积累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像姜葆夫教授那样博学而又历尽苦难也要保持着一位文人风骨的作家,我们还能数出几个?像李贯通当年把房门锁上、窗户塞严一人藏在屋内昼夜苦干的精神,我们还有吗?不要说学贯中西了,我们有几个能够通一门外语?有谁还在 “天天向上”地“好好学习”?如今能够读懂古文又有几个?缺乏常识,没有风骨,还怎么能够期待眼界与境界?而眼界与境界,也许正是制约我们文学创作的最根本因素。眼低怎能手高?我们需要在逆境中能够保持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的真正的作家,我们需要在迷雾弥天的时候能够看清未来、看透历史与现实的真相,并且敢于面对敢于直言的作家,我们需要有良心有责任感、有牺牲与献身精神的作家。只有有了这样的作家,我们才可以说济宁文学创作的黄金季节到来了……
还有,就是在文学的创作上,我们有的经不住长时间的寂寞和挫折,中途撤退,让队伍减员。如纪广洋、于常印的离开诗歌创作的行列,如杜辉、李养玉中断了小说的创作等。尤其是杜辉、李养玉,都有着相当高的写作天分,也写出过一些精彩的小说,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都在最近几年沉寂了。再如李雁鸣、周伟,手中的那支诚挚而又能准确地写人状物从而能够感动读者的笔,近年来也有些生涩了。是环境还是年龄让其淡薄或失去了创作的心境?我衷心地期待着他们的重新振作。还有一种现象是太急功近利,总想一夜成名或一炮打响,写得太过匆忙。这样也许会一时有点小热闹,但是最终只能因其过于匆忙而让自己的园地荒芜。
另一种不能忽视的现象是一部分已经取得成功的作家,缺少了创作动力与创作激情或过早地退出了写作行列、或作品明显减少。如散文家张九韶,自担任市政协领导职务以后,散文的创作明显减速,这是相当可惜的。再如小说家曲春礼,写过孔子传等三传之后,干脆就沉寂了。我市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李贯通,近些年的创作数量也在明显减少,少了一些当年的锐气。这方面,姜葆夫教授值得我们学习。他在即使身体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的情况下,还在力所能及的动笔和学习接收新鲜事物。如前不久大病住院,出院后瘦得仅有三十多公斤,一能动就又拿起了笔。
一句话,文学创作必须要有一个自由健康博大的心灵,必须要有一种耐得住长期寂寞,呕心沥血、埋头苦干长干的精神。因此,只要决心从事这项事业,必须得首先解放了自己。
文学的生长土壤与作家的生存环境
得说说我们文学的生长土壤与作家的生存环境了。
还记得我们引为骄傲的孔子的周游列国吗?好好的他为什么会抛家舍业四处奔波?还不是因为鲁国的环境不好,没法施展自己的才干,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才远走他乡的?那个敢发千古一声的文学家贾凫西,不也是不能容于家乡曲阜而迫迁于兖州的吗?在我们继承他们精神遗产的同时,当然也要反思一下他们的当时生存环境。这样,我们就会清醒而又自觉地为我们的作家们营造起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来。
我们应当给作家们以应有的尊重。这个尊重,首要的当然是尊重他们的劳动。作为在精神领域里耕作的作家们,他们往往是敏感而易于受伤的。有时得到一点尊重就会使他们感到温暖与畅意,就会激发起劳动的干劲来。
我们应当给作家们以应有的理解。他们大多是在业余的时间里来从事文学的创作,他们也许不能承受太多会议与应酬,因为这样会占去了大脑思考的时间。他们也许不大够合群,但是他们确实有着与人为善的心地。他们并不想在做人处事上标新立异,只是想能够安静地在精神天地里自由地徜徉。
我们应当为作家们尽可能地解决一些困难,起码是不要人为地增加他们的困难与烦恼。比如住房,比如评职称,比如子女的就学就业,比如正常的升迁等等,即使不照顾他们,也别格外亏待他们。如果能够主动地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那他们是一定会以成倍的成绩作报偿的。我相信,我们这个文化名市,一定会让这些文化人心情舒畅的。有时,心情舒畅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那时,心情舒畅的作家们不是可以奉献出一件件“硬件”来让我们这个文化名市更有底气的吗?再说啦,一个没有名作家的文化名市似乎是有些缺憾的。
当然,我们还应该建立起与我们的文化名市相称的文学艺术创作基地,为作家们构建发表作品的园地。十多年间,我市除了济宁日报星期天刊团结凝聚了一大批作家作者之外,还没有其他园地承担这一任务。此外,我们还应当为作家艺术家们提供良好的创作条件,打破作家队伍中的大锅饭现象,并用奖惩分明的签约等方式,为作家们建立起一种真正的竞争机制,以求激发起他们更大创造能量,为我们的文化名市提供层出不穷的文学精品、文化名牌。试想,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能够让作家安心创作的基地,如果我们有一份在全省全国叫响的刊物,如果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出版社(可叫春秋出版社),那我们的文学创作一定会是另外一种气象了。
最近,我接到了作家王方晨的一封来信,他在信中说:“当年离开济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在外地,又有一项好处,可以放得开。我历来不怕吃苦。艰苦可以锻炼自己。这是闯出来了。闯不出来,就惨了。”这让我想到当年李贯通的离开济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最近几年涌现出来的这三位有实力、有实绩的小说家中的两位王方晨、岳喜虎,都已离开了济宁,而且是在离开济宁之后出了成绩的。散文家王开岭现在正在中央电视台帮忙,听说也要离开济宁。最近看到曾是济宁师专美术系系主任的刘远智教授出版了他的第九部书《刘远智水彩画》。他现在已经是中国著名的水彩画家。当然,我们也没能留住他。他到了中国矿业大学后,顺利评上了职称,迅速获得了教学科研基金,当然也就如鱼得水般地进步不断、成果不断,不断地出了九部书,还在美术教学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现象也许各有各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引起警惕,反省一下人才的成长与生存环境问题,看看我们的作家们是否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看看他们是否心情舒畅。一个让人心情舒畅的地方是美丽的地方,美丽的地方人们不仅不会离开、还会让四方的人才趋之若鹜。
我们将朱复勘艺术馆建在了济宁,我们拿出了不少的职位吸引来外省的高学历人才———这种有远见的举动不是已经发挥了超出事件本身的更大的社会效益了吗?
关注新生力量的成长与发展
在济宁籍的作家当中,已经有两位三次获得过真正的国家级文学奖:鱼台籍作家李贯通继小说《洞天》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之后,中篇小说《天缺一角》又获得鲁迅文学奖,兖州籍诗人曹宇翔的诗集同样获得鲁迅文学奖。
这是济宁文学的光荣。当然,一部作品的意义并不在获奖与否,《红楼梦》没获过什么奖,照样会千古流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新人新作应当受到我们格外的关注与重视。锦上添花的事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更应该做,而且要快做,越早越好。
王方晨、岳喜虎、卢金地、王开岭,这是我们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年轻作家,他们都已闯出了一番天地,但是却也正处于爬坡的当儿,也许我们的一分理解、一分支持,会给他们以更大的前进的力量,会促使他们更快的前进。他们之外,还有一批虽然没有成名,却有着相当潜力的业余作者,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也更加需要社会与大家的理解与帮助,如写诗的张侗、李克实、王青春、姜良纲,写小说的崔新泉,写散文的孙继泉、张瑞,写报告文学的窦洪涛等。
还有一批重要的作品,不应被我们忽略———王方晨的小说《说着玩儿》、《扑满》、《麻烦你跟我走一趟》、《生命是一只香油瓶》(发表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并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选载);岳喜虎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另一只手》、《保险柜》,发表在《十月》上的中篇小说《天凉好个秋》,被《小说选刊》选发的小说《地铁台阶上的赤脚医生》等;卢金地发表在《十月》上的中篇小说《斗地主》、《笛声悠扬》;陈宝旗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的小说《罪人》;王开岭的散文集《激动的舌头》、《跟随勇敢的心》;王黎明的诗集 ;李木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遥远的军旅》、《微山湖上静悄悄》,发表在《十月》上的《杏坛》,发表在《当代》上的《不凋的激情》,发表在《大家》上的《曲阜古柏》、《蜿蜒的圣脉》,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的《孔林随想》,被《新华文摘》、《散文选刊》选载的《寻味峄山》、《圣地三女性》、《木皮散客贾凫西》、《不屈的歌者食指》、《李白当年生活的好吗?》,被二十世纪文化散文系列丛书收入的《在山水皇帝之间———孔尚任》等。
时间将会作出真正的选择,因为一茬一茬的读者接力赛一样地在对作家与作品进行着最有情也最无情的选择。济宁的作家们与济宁作家所创作出的作品,都将经受这严格而又公正的选择。我们会在济宁前进的道路上看到济宁作家留下的足迹,我们也一定会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宝库里,看到济宁作家创造出的作品。
我们期待着济宁文学创作的全面腾飞。